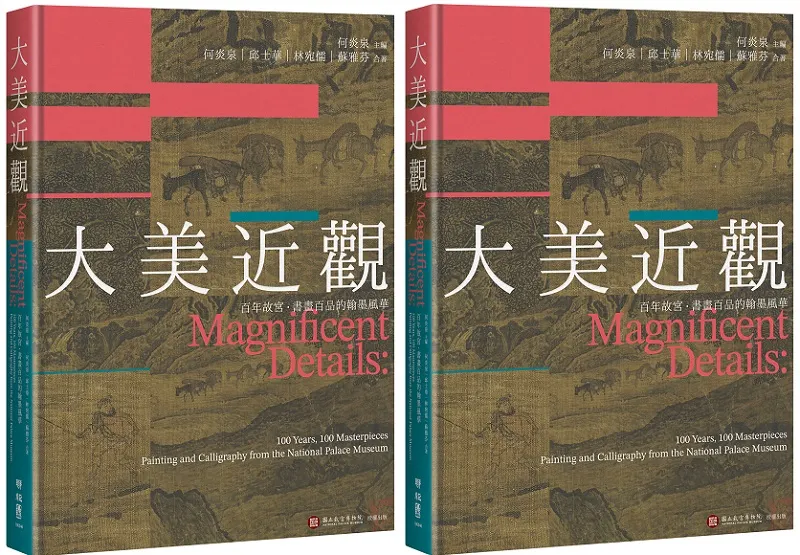1925年10月10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成立,開啟中華民國博物館史及藝術史的新篇章。1965年故宮新館在臺北外雙溪落成揭幕,確立在臺生根與發展,如今也一甲子過去了。在歷代故宮人的努力與守護下,經歷了南遷、渡海、開館等重要篇章,不但躍昇為世界級重要博物館,亦成為台灣與世界的共同記憶,百年院慶並不非終點,而是繼續前行的新起點。
故宮博物院成立後,帝王私人收藏公諸於世,對於書畫史研究至關重要,專家學者有機會接觸原作,不過影響有限。根據前副院長何傳馨(1951-2024)研究指出,舉世聞名的范寬(約950-1032後)〈谿山行旅圖〉,在1932年133期《故宮週刊》登出圖版,不過是繼36期的范寬〈群峰雪霽圖〉、91期的范寬〈行旅圖〉,及131期的范寬〈雪山蕭寺〉之後,才刊登出來的范寬作品。以現今的研究成果看來,四件作品是完全不同等級,反映當時對於范寬的認知。范寬〈谿山行旅圖〉在《石渠寶笈》僅列次等,或許頂著正統頭銜的《石渠寶笈》,在當時還是有著一定的權威性。事實上,即使是今日藝術史昌明的時代,《石渠寶笈》中仍然保有不少真知灼見,尤其是整體書畫史的品評標準。
1949年〈谿山行旅圖〉隨同其他文物運到臺灣,在清查遷台文物工作完成後,編委會於1955年著手編印《故宮書畫錄》。〈谿山行旅圖〉收在畫軸一卷,依《石渠寶笈》註明為無款。隨著文物安置完成後,在台中北溝也開放參觀研究,迎來第一波重要的西方學者,以不同於傳統的藝術史觀點,重新審視這批珍貴的書畫典藏,獲得不少重要成果。根據前副院長李霖燦(1913-1999)於1958年以〈谿山行旅圖〉為題發表的故宮讀畫劄記,即提到這幅畫在當時已廣為國內外學者讚賞,聲名顯赫。此時期故宮的研究人員也開始以中西合併的方法,更細緻地分出書畫等地,讓品評標準更加精準。接著,許多留學海外的年輕學者紛紛歸國,在各大教學機構成立研究單位,藝術史在台灣的發展速度相當蓬勃。當然,這批學者中也有進入故宮工作,成為此時期研究的生力軍,將西方的風格分析與圖像學引進書畫研究中,獲得豐碩的成果。這股研究趨勢持續至今,無論在展覽策畫或是論文寫作上,都還可以看到影響力。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故宮出借131件文物赴歐展覽,我有話要說
|
更多文章
)
清代《石渠寶笈》就開始對這批書畫分等列次,故宮研究人員在此基礎完成書畫編目的基礎工作,成為日後研究的重要基礎,也對於作品做出新的品質判斷,在《故宮書畫錄》中以正、簡目來區分,實際的成果可在參考《故宮書畫圖錄》與《故宮歷代法書全集》兩套巨著。這對於該時期書畫研究意義非凡,畢竟當時其他博物館的藏品皆無如此有計劃的整理與出版,可說是相當前瞻的工作,嘉惠後人。後續的研究人員透過展覽與研究,加深對於文物的認識,同時也在書畫上進行分級的修正,2005底完成院內暫行分級。2008年開始實質的文物分級審查,由文建會(文化部前身)古物審議委員,配合歷次的書畫展覽,進行書面審議及實物勘驗,訂定出國寶和重要古物。目前所完成公告的書畫國寶、重要古物及一般古物等級,奠基在前人的貢獻與努力下,又比過去更加精準。儘管提報的是典藏單位,分級的理由及意見也是院內研究同仁撰寫,不過最終審議的委員是由文化部召集,來自相關領域的代表,補全故宮以外的意見,可謂相當全面。目前已經大致完成的書畫分級,完全能夠代表故宮來臺後的在地化發展與研究成果。試想如果當年並未搬遷,就不會有北溝的開放,更不會吸引大批學子出國學習,當然也沒有欣欣向榮的藝術史學科,更不會有目前豐碩的分級成果。
2002年起,故宮加入國科會所主導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後續又參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直至2012年。推動數位典藏工作的十年中,院內相關處室積極參與,依文物類型和業務分工的特性,建立了文物知識數位化和文物資訊系統基礎,共建了21個資料庫。這些資料庫有助於文物管理、策展研究、出版授權、推廣行銷等,對外則可提供民眾或業者查詢,成為相關工作的基礎,發揮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書畫史研究從古自今有過幾個重大轉變。書法一開始就是非具象藝術,長期以來都是以筆墨為核心,探討書家與作品的關係。同樣以毛筆為工具的繪畫,雖然起初帶著具象的功能與目的,不過因為筆法共享的緣故,導致「書畫同源」的結果。這樣的發展事實,讓書法中的率先成熟的筆墨技巧與理論,開始滲透進繪畫中。事實上,古代畫論也以作品中的筆墨為主要討論內容,顯示繪畫也是很早就開始走向非具象的發展,如蘇軾(1037-1101)〈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大力讚賞王維(699-761)「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據此順勢發展出元、明、清的文人畫。
發展過程中,數千年來位居賞鑑核心的筆墨看似堅不可破,卻在清末被列強完全擊潰,加上新式書寫工具所引起的筆墨疏離感,使得多數研究者紛紛轉向,尋求其他更先進的研究方法。故宮博院成立後,皇室私藏作品的公開展示,似乎出現一線轉機,最終還是因推廣難度而告終。儘管後來出現照相與印刷技術,不過影像的分辨率與逼真度仍有所限制。直到21世紀初的數位計畫才算真正出現契機,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資料累積與技術升級,數位影像已經進步到可以超越人類的視覺感知。這樣的便利性,就書畫研究史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利基。以王羲之(303-361)為例,終日與毛筆為伍的古代研究者儘管讀過很多書,然從所論述的相關文字中便能發現,多數人終其一身都沒見過書聖的作品或可靠摹本,看似豐碩的成果往往只是抄抄寫寫。際遇好些的文人,如米芾(1052-1108)、趙孟頫(1254-1322)、文徵明(1470-1559)、董其昌(1555-1636)等人,有機會看到一兩件就三生有幸了,豈有可能像今天隨便檢索一下,就可以將右軍的書法「倩影」瞬間召喚到手機、平板或電腦的螢幕上來,完全進入一個「不可思議」的研究新境界。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故宮出借131件文物赴歐展覽,我有話要說
|
更多文章
)
隨著數位照相技術的突飛猛進,研究者終於有機會可以看清楚點畫中的細微變化,透過放大及修圖等功能,甚至能強化出許多肉眼所不容易看到的重要訊息。對於博物中館隔層玻璃展出原作更是如此,無論透光率多高,加上幽微的燈光及低色溫照明的要求,總是會有許多的關鍵訊息被遮蔽掉。即使申請文物的特別提件參觀,獲得面對於原作的寶貴機會,也同樣會因為燈光、時間等各種限制,很難好好地仔細觀察。現代人的機會來了嗎?答案雖然很肯定,但關鍵是能否把握住。畢竟目前還是處在一個筆墨疏離與不通的時代,如果仍舊停留在過去的思維模式與研究視角,那麼擺在眼前的影像訊息無論多麼難能可貴,就只會成為大家口中的「筆墨」,具體究竟是什麼就很難說了,大概又是另外一個瞎子摸象的故事。
筆墨究竟是什麼?著名書畫鑑賞家王季遷(1907-2003):「中國繪畫則像歌劇,此時聲音是主要因素」、「中國的筆墨如同聲音訓練,包含極多的練習和功夫,才能達到精通的地步」。困難在於筆墨鑑賞能力如何培養,從古至今都是大哉問,絕非簡單透過寫字、畫畫、收藏或研究等就能充分掌握。親自動手寫字畫畫,或多看歷代傑作,確實能增進對傳統筆墨的瞭解,但理解到什麼程度就因人而異。此外,在歷代文人的繼承、詮釋與發展下,「筆墨」也以種種面目輪番出現在舞台上,老早幻化出許多分身,讓後人更加難窺其堂奧。
面對環境的劇烈變化,藝術史研究方法近年來似乎有所調整,但整體思維還是偏向舊有模式,許多人還是習慣透過紙本印刷來研究。當然,不在乎筆墨或不瞭解其奧妙精微的人而言,普通出版品也確實足夠。由於印刷解析度相對有限,遠不如數位影像來得精細與真實,在這種品質下看看母題、造型、結構、空間等都還游刃有餘,但對於作品中最精彩的筆墨就無異於隔層紗。不僅在文物觀察模式上出現天翻地覆的變革,現代也進入資料量爆炸的時代,蒐集資料的速度也是前所未見,老實說這些都已經超越人類的限制,若繼續採用傳統上霧裏看花的心態來看待藝術品,當然很難有所突破。當全新數位高科技的獵物出現時,還在思索如何利用過去的類比工具來抓捕,豈不是有點緣木求魚的味道。
一件作品為何讓人感到精彩?為何感動?為何偉大?必定有其原因,不會平白無故地達到上述的審美品質,也絕非單靠外在條件就能脫穎而出。許多與藝術品質無關的外在條件與特徵,往往都能透過模仿輕易完成,唯有筆墨才能與創作者緊密結合,展現出獨一無二的特質。正值百年院慶之際,特別精選出書法、山水、人物、花鳥共一百件共襄盛舉,其中包含前人的成果,也有當前的考量。書中將透過實際的觀看引導,向讀者介紹作品中最精采動人的部分,試圖走出屬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書畫研究新方向。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故宮出借131件文物赴歐展覽,我有話要說
|
更多文章
)
*作者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處長,波士頓大學藝術與建築史博士,本文選自作者與邱士華、林宛儒、蘇雅芬合著,作者主編之《大美近觀:百年故宮.書畫百品的翰墨風華》(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