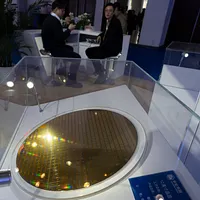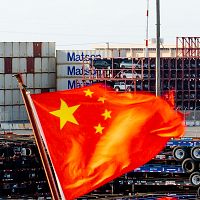賴清德總統不久前提出「民主制度要不斷打掉雜質」的說法,初聽之下似乎是一句正向的改革語言,強調政治清明與制度革新。然而,在當前社會氛圍與政治對立持續升高的脈絡下,這句話所承載的政治隱喻與象徵意涵,值得更審慎地檢視。
語言塑造現實,特別是當它來自國家最高領導人之口。當政府訴求「清除雜質」作為民主深化的手段,問題便轉化為:誰是雜質?由誰界定?哪些聲音被視為異常、哪些行動被暗示為應被剷除?這些問題的答案,關乎的是我們對民主政治的基本想像。
當語言預設敵我,民主風險也隨之升高
「打掉雜質」這類話語,其實並不陌生。歷史上極權體制常用類似的語言架構來合理化對異議分子的排除。例如納粹德國以「民族純化」為名將猶太人、左翼份子與各種異己標示為「毒素」與「病原體」;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也習慣以「階級敵人」與「反革命份子」的概念進行語言上的標靶,隨後配合政治清洗與強制消音。
這類語言有一共同特徵:它們看似針對結構、針對制度、針對效率,但實際上卻透過模糊的隱喻,把異議群體轉化為「應清除」的象徵。他們不再只是「意見不同者」,而是「破壞整體的人」,這使後續的政治壓制與動員行為具有正當性與道德優勢。
台灣當然不是極權國家,但當總統的語言帶有隱性分類、去人化的意味,而社會與媒體又未加批判地跟進,便可能在不知不覺間讓民主社會滑向對多元聲音容忍度降低的方向。
罷免運動成為「雜質」隱喻的對象?
觀察最近啟動的「大罷免行動」,不難發現這波由基層民間發起、針對部分立委的不信任動員,雖然程序合法、訴求明確,但卻遭遇前所未見的行政干預與輿論壓力。例如,部分志工與主辦人被警方以各種理由約談、連署據點遭施壓、甚至有民代質疑罷免資金來源「不單純」。原本屬於公民基本政治參與的制度性工具,彷彿成了需要警戒與管制的「異常行動」。
與此同時,民進黨過去在在野期間曾積極使用罷免制度,例如罷韓國瑜、罷黃捷、罷王浩宇等案例,不僅未遭遇相同層級的行政干預,甚至獲得媒體與知識界的高度支持。如今情勢逆轉,不禁讓人質疑:執政者口中的「雜質」,是否指涉的正是這些無法掌控的基層異議聲音?
若我們把賴總統「打掉雜質」的語言,與政府系統對罷免行動的回應放在同一脈絡來看,不難發現一種潛在邏輯:罷免不再被視為民意的正常表達,而是體制內部的「異常分子」;公民參與不再是民主的活力展現,而是必須加以控管的「不確定因子」。
民主能不能承受「非理想民意」的出現?
值得提醒的是,罷免制度本身即是台灣民主憲政設計中的重要一環,它保障選民在任期中對公職人員的不滿有補救管道,讓代議制度中的民意扭曲能有機會被修正。雖然罷免行動在實務上常有政治操作空間,但制度本身不應因使用者的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差別對待。
事實上,民主制度的本質之一,就是容納那些不被期待、甚至令人感到不安的參與。政府若只接受有組織、有禮貌、體制友善的參與,而對自發、不符主流敘事的聲音產生敵意,這樣的民主就已經喪失其本質的開放性與多元性。
換句話說,真正的民主成熟,不是體現在對於支持者的擁抱,而是在面對反對者時的容忍與謙卑。
誰才是民主裡真正的雜質?
我們不否認政府有權倡議改革、捍衛制度正義,甚至可以批評不實訊息與惡意動員。但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上—公民行使基本權利的行為不應被標示為「雜質」、不應因立場不同就被制度性冷處理或邊緣化。
語言不是無害的。當國家領導人用「打掉雜質」來形容改革願景時,也許只是一種比喻,但在具體政治實踐中,這種語言會形塑一種治理傾向:只要不符主流就可能被視為破壞者,只要不在既有體制內就可能被排除、被懷疑,甚至被打壓。
今日罷免行動的推展過程已成為試金石—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人民對立委的審判,更是體制是否容納多元民意、是否容忍異議能量的壓力測試。
「打掉雜質」的語言也許能贏得一時政治掌聲,但若它最終變成政權排除異議的口號,那麼真正需要被民主制度排除的,恐怕不是人民的聲音,而是對反對聲音失去耐性的統治習慣與語言傲慢。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的「團結」,讓人不寒而慄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