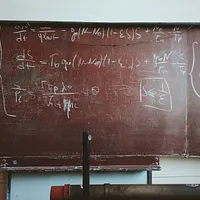算是後見之明吧!回頭想想,2005年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出版的《地球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以及他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政策教授Michael Mandelbaum共同撰寫、2011年出版的「我們曾經輝煌」 (That Used to Be Us)一書中,已然可以發現美國內陸地區的集體挫折感以及他們對美國沒落的喟嘆。而「我們曾經輝煌」,和川普此次大選的口號:「再創美國榮耀」(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是不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呢?另外,大前研一所撰寫的M型社會,也已隱隱約約地指出了,當美國式民主賴以為繼的中產階級已經潰散時,民主來能不變質嗎?一向自詡統領中產階級的美國政治菁英,竟然沒有默察到中產階級消逝對美國民主選舉的衝擊?

反觀台灣,社會M型化,中產階級的消逝,幾乎也已經是個存在的事實了。依照亞里斯多德以降的西方古典民主理論,或是中國古代「有恆產有恆心」的說法,龐大的中產階級,不僅僅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實施民主政治的要件。這兒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定義,不只是指涉有一定的恆產(譬如:一棟足以避風遮雨,享受家庭生活的房子),也指涉接受過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就業能力,而中產階級的堅實化,當然有賴於政府能提供一個公平追求知識、財富和自我發展機會的環境,而不是透過各種政策和命令,強迫大家回到相同的矮簷下。用經濟常識的說法,維繫中產階級的最佳策略是要先求成長,再求分配的平均。
無論如何,當台灣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時,當台灣的財富愈往前面百分之五的人集中時,執政的團隊卻還堅持加徵房地產稅捐,溯及既往地砍掉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年金,忙著清算和70年前發生的悲劇無關的政黨成員,斬斷和大陸經貿觀光往來的渠道,卻拿不出彌補產業缺口的對策;斤斤計較勞工的七天假、卻不思如何提高勞工的所得;搶著進口極可能含有輻射殘留的日本食品,卻不思考開放對台灣消費者的影響.....。這些作為,是不是會加速了財富集中的趨勢?會不化讓老齡階層通通淪為下流老人?會不會加速台灣中產階級的崩解?會不會強化了社會上的憤怨之心?會不會在下一次大選裡,培養出一個又一個的政治狂人? (相關報導: 韋安觀點:別裝了!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川普」 | 更多文章 )
社會期望值下的虛擬美國 VS. 大男人主義與歧視的真實美國
一次大戰後,美國的國家認同是非常堅實的,而二戰以後的世界警察角色更是美國兩黨共同遵循的外交政策指導原則,這就是學者所謂的美國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Bipartisan Foreign Policy)。外交既不是選舉的重大議題,經濟和貨幣政策往往又不是一般選民能夠理解的,再加上候選人對財經政策也搞不太清楚,因此,過往總統大選的議題往往是墮胎、同性戀等雞皮蒜毛的問題。川普反其道而行,他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策略,是撇開墮胎、同性戀等老掉牙的議題,挖掘出選民心裡深處某些反社會期望值的真正想法:那便是大男人主義、種族歧視、反移民、外交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反全球化、反貿易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