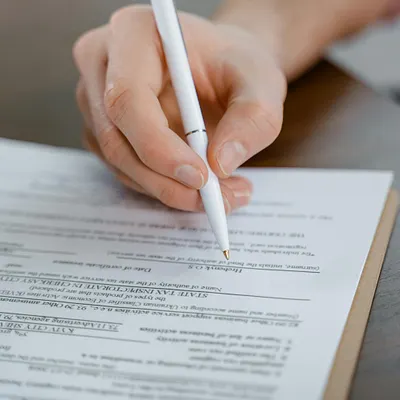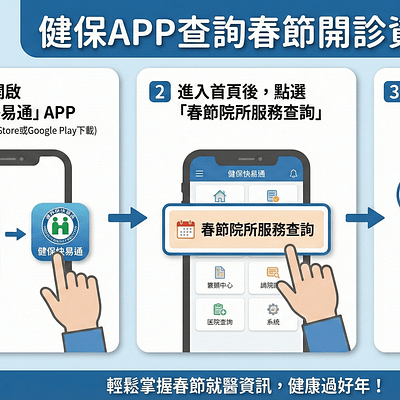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那一點星星是火,如果那片原是草原。
二○二二年十月十日早上十點,一個由「趙明河義士研究會」以及「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合辦的追慕儀式在台北的金山南路與信義路交叉口附近的中華電信大樓側邊一片圍牆前舉行。合辦的單位都與韓國有關,他們追慕的人名為趙明河,趙是朝鮮民族的大姓,看姓名以及主辦單位的性質,大概也可以猜測他當是朝鮮民族的人,其生平事蹟應當與重要的公領域事務有關。而且,這件重要的公共事務應該與台北鬧區的這一片圍牆有關,否則,儀式不會在此場地舉行。
但是「趙明河」這三個字確實陌生,聽過這個姓名的台灣人恐怕屈指可數。這個判斷也不是我說的,而是我的一位韓國朋友,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文學科的孟教授所說的。我們認識已三十多年了,在韓國漢城(當時的名稱,現在已名為首爾)相識,當時,我仍是博士生,因緣際會,恰好有機會可以到韓國教書。一九八○年中葉以後的國際冷戰體系已鬆動,蘇東巨變雖然還沒有發生,但共產國家勢必要變的趨勢已經很清楚。中共與南韓眉來眼去,暗通款曲,也不是秘密。只是礙於朝鮮人民共和國(北韓)的存在,勾搭總不能暢快。我在這個尷尬的時間點到了韓國這個國度,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時間點。我在此領略到不同的校園文化,台、韓同為東亞小國,對美、日、中強權的態度卻截然不同,而這個國家和我們的關係又是那麼的密切。
韓國(正式的名稱為大韓民國)和我們的關係一向很緊密,緊密到曾經可以視為同一國,這樣的敘述不是情感語言,而是事實的語言。我這裡說的「我們」是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也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那個國家而言。凡經歷過冷戰歲月的人,應當都聽過「中韓兩國是兄弟之邦」的外交辭令,而這個外交辭令施用的範圍還真是廣,在商業領域、學術領域、政治領域,只要有兩國人士在場,這樣的語言幾乎可以確定,一定會出現。兄弟!兄弟!這兩個字如果沒有出口,會就還沒有開完。而當時所說的「中」指的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韓」是大韓民國,而不是朝鮮人民共和國,這樣的指謂也是很清楚的。
平心靜氣一想,當領土僅剩台灣(含周邊島嶼)的國家還被視為代表中國時,底氣是有些虛的。當時與台灣有邦交的國家不少,美國、日本是台灣生存依繫的友邦,當然重要。但如要論歷史的關係、文化的結構、現世的命運,確實沒有哪一個國家比韓國更關係密切了。甲午(日清)戰爭,滿清戰敗,台灣被割讓,韓國被獨立,兩地同時從華夏秩序脫鉤出來。
(相關報導:
他們的手臂曾經創造奇蹟,但却像定時炸彈:《百萬金臂》選摘(1)
|
更多文章
)
二戰後不久,中國與韓國都爆發內戰,兩國又都成了分裂國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和在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南的大韓民國很自然地被擺在國際地圖上的準同盟關係,同樣被劃入太平洋第一島鏈的美國秩序的圈子內。但在情感上,由於兩國獨特的歷史淵源,更可以說是比同盟關係還親近。當時兩國的高級官員,不論文武,通常有抗戰時期的合作關係。如曾為駐華大使的金信即是韓國臨時政府主席的金九的兒子,今日韓國的漢學家或中國通人才,十之八九都有台灣經驗—包括前韓國大統領朴槿惠(朴正熙女兒)都曾在台灣留學幾年,學習中文。
中韓兩國(斷交前台韓的稱呼)更密切的關係還不是冷戰時期,而是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三十四年期間。一九一一年,前十年被獨立的大韓帝國在拖過被日本帝國手銬腳鐐的歲月後,終於被合邦,成為大日本帝國的領土。而更早在韓國被獨立的同時,台灣早已被滿清割讓,成為日本帝國的新領土。換言之,在一個奇特而扭曲的歲月,台韓兩地人民曾是同一國的國民,他們在同一面國旗、同一首國歌、同一種國語下過活,這顯然不是兩地人民自願的選擇。但殘酷的國際局勢將隔著大海的兩地壓縮在一起,這樣的同國經驗顯然不是順著兩地的歷史脈絡自然發展出來的,它成了尷尬的過去。像是隱疾,有痛,但不便說出。也像從未打開的黑盒子,是禮物?是災禍?還是不相干的一坏土或一杯水?無人知道。
但既然同國了,憋憋扭扭,也同胞了三十四年。雖然被殖民的政治經驗是苦澀的,但災禍一旦被正視了,成為知識的對象,它的性質也就脫胎換骨了,具有客觀的意義。台韓兩地當然有各自的文化傳承與歷史脈絡,韓國這個位居東亞半島的國家更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質。但無可否認地,兩者共享的文化成分與歷史經驗還是很多:漢字、書畫、儒佛兩教、律令等等,還有在東方唯一帝國主義國家日本統治下的共在關係,這些複雜的因素使得兩地的相互了解,彼此映照,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但或許這段被殖民的經驗過於尷尬,或許源於冷戰體制下必然會出現的體制性的思考,能夠站在當代的、血性的、情動的、且具有歷史社會結構穿透性的分析,還真是少見。
台灣的公共團體中,會注意到台韓兩地在殖民時期以及在冷戰時期的共同命運者,大概只有左翼團體。左翼團體通常具有國際主義的兄弟情懷,有社會、經濟關係的分析能力,也有批判的實踐能力,台韓關係無疑是他們思考政治問題時常會出現的焦點。但一來,左翼團體在台灣的聲勢不夠大;二來,左翼團體的關懷一樣有選擇性,不見得每件重要的議題都是成比例地受到重視。趙明河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它是發生在島嶼上的一樁「跨區域」事件,一位朝鮮民族的人民跑到異地異語的島嶼,幹了一件可以成為集體記憶的事件。但它卻像是埋在流沙中一座廢棄的堡壘,與歲月共老,在風沙的流動中同被遺忘。
埋在流沙中的城堡到底重不重要呢?關鍵在這座城堡能夠傳達什麼訊息。趙明河所以被韓國人記得,還要到異國一片城牆下追慕,乃因他被視為韓國人的民族英雄,是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烈士。在日本殖民大韓民國時期,韓國反抗運動中有組特殊的形式,此即暗殺行動。暗殺是各國革命黨人喜歡運用的手段,梁啟超即曾大力讚美,力言只要伏尸一人,流血幾步,局面就可打開。清末革命黨人即多暗殺滿清權貴事件,抗戰期間,敵偽區也常發生漢奸被殺。但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台人早期的反抗運動頗多採取武裝暴動的策略,「土匪」不少,暗殺事則較少聽聞。韓人不同,暗殺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手段,他們有「四大暗殺事件」的紀錄。
(相關報導:
他們的手臂曾經創造奇蹟,但却像定時炸彈:《百萬金臂》選摘(1)
|
更多文章
)
趙明河(左)與他刺殺未果的久邇宮邦彥親王(右)。(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官網)
韓人的四大暗殺事件,最大也最赫赫有名者,即是安重根的暗殺伊藤博文事件。一九○九年,首任朝鮮統監府統監的伊藤博文正率團,抵達哈爾濱火車站,要與俄國官員談判,商量日韓合併事宜。日本團一行剛下車,儀式尚未進行,即砰然槍擊聲起,伊藤博文中彈數槍,當場死亡。兇手安重根立刻被抓,送進旅順監獄,終受絞刑。這場暗殺行動的計畫夠詳密,地點夠好,時間夠準,震撼效果也夠強,它成了朝鮮民族一首永恆的聖歌。
第二樁成功暗殺的例子是一九三二年,朝鮮烈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暗殺當時駐滬司令白川義則的事件。這次事件發生的時間是日軍剛在上海打完一二八「懲戒」戰役不久,右翼氣焰直衝雲天之際。那年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長節,在華日軍假虹口公園大肆慶祝之際,一個殖民地的憤怒青年以炸藥陳述了另一個故事。白川義則不久即傷重不治而亡,當場受傷的還有幾位日本高階文武官員,其中包括駐華公使重光葵,他跛了一隻腳,日本戰敗投降時,他是簽署降書的外相。這場暗殺事件的時間、地點同樣掌握精準,震撼效果同樣巨大。
這兩則暗殺事件都發生在中國境內,由於中日關係在這段期間非常惡劣,所以兩位朝鮮刺客的行為不但對當時被壓迫的朝鮮人民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它對近代以來長期被日本軍閥凌辱的華人來說,自然也是大大地出了一口氣。另外兩則暗殺事件是未成功的刺客故事,第三件是發生於日本東京櫻井門的大逆事件,一位朝鮮青年李奉昌於一九三二年,埋伏於皇宮的櫻井門附近,擬暗殺日本天皇,為朝鮮人民復仇。事不成,被擄,下場當然只有死亡一途。這場暗殺事件雖然流產,但因為暗殺層級夠高,所以它會被朝鮮人民傳頌,也可想像而知。
第四件刺客事件顯然沒有前三件那般轟動,事件的脈絡如草蛇灰線,或者說如大漠中的地下水流,若斷若續,乍隱乍現。但既然被排列在一起,內涵也不可能不複雜。更重要地,它發生在同屬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四日,一位化名為明河豐雄的朝鮮青年,趁著時為檢閱日本帝國陸軍來台的久邇宮邦彥親王巡視臺中州時,在當時的臺中州立圖書館(今合作金庫銀行台中分行)前的行道樹下想要行刺此親王,匕首一現,即告失風,當場被捕。一說,久邇宮邦彥親王後來曾入院治療,其病可能和這位朝鮮青年的行刺有關。
明河豐雄即是朝鮮青年趙明河的日本名字,他在朝鮮反抗運動組織中的經歷不明,他的刺殺手法也不夠有效(在警衛森嚴下,想以短刀行刺),他在台半年的行蹤也不夠清楚。但久邇宮邦彥親王是當時天皇的岳父,可不是小人物。所以此一號稱「台中不敬事件」的事一發生,暗殺目標無恙,一群臺灣總督府的高級官僚卻紛紛中箭落馬了。其中包括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總務長官後藤文夫、警務局長本山文平、臺中州知事佐藤續等人都相繼引咎辭職。
趙明河暗殺事件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一定是大事件,總督都辭職了,官僚體系也被震歪了,事情怎麼小得了?但現在的台灣人知此事者確實不多,我在清華大學與那位外國語大學中語系的孟姓朋友初見面時,他提及他和一位在台任教的金姓韓籍教授每向台灣人提及此事時,台人的回應都是「前所未聞」。這位金姓的韓籍教授曾留學臺大,算是我的學弟,他對趙明河事件非常關心,長期追蹤此事的始末。
(相關報導:
他們的手臂曾經創造奇蹟,但却像定時炸彈:《百萬金臂》選摘(1)
|
更多文章
)
一九二八年離現在都快百年了,一般台灣人不會知道那場不敬事件,並不意外。我例外,我聽過此事,而且一度還時常想起此刺殺未遂的政治事件到底具有何種意義。我最初的訊息是從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那邊看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編著的《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他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四日條目下,記載了如下的內容:
久邇宮邦彥親王奉命來台檢閱陸軍,途經台中市,韓國人趙明河攜短刀行刺未果,當場被捕。七月十八日定讞判處死刑。(七月十八日執行)。
葉榮鐘住台中,行刺事件發生的地點與臺灣民眾黨成立的地點聚英樓酒家,相去不遠。臺灣民眾黨剛於一九二七年六月成立,兩樁事件相去的時間不到一年,也很近。葉榮鐘是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台人反抗運動的重要人物,他對發生於台中的這樁事件不可能不關心。但後加括弧的「七月十八日執行」,他說的趙明河死刑執行日期與韓人的理解不同,不知何故?可能是筆誤,因為同一天判刑定讞,同一天執行,不太合理。
我不知道其他人編寫歷史年表時,是否會將此事列進去。但葉榮鐘那輩的台灣反抗運動人物的鬥爭目標很明確:日本帝國的殖民體制,他們對台韓兩地的共同命運感也有一定的認知。葉榮鐘在日本殖民的晚期,即曾和臺灣文化協會的同志拜訪過朝鮮,且渡過鴨綠江,進入過東北。他們大概沒有和朝鮮族的反抗團體形成堅強的同盟關係,但互通聲氣一定是有的。情感不一定要私誼的,共同的歷史處境也會引發同仇敵愾的情感。
趙明河行刺親王的地點就在我中學讀書的那座城市的市中心,地點離我們當時那群高中生時常偷偷瞄望的臺中女中不遠,這個行刺地點是後來才知曉的。目前已立有石碑,簡要述及此事。我初讀葉榮鐘的文字時,對當時「不敬事件」的內涵卻是藐藐茫茫,摸不著邊。曾幾度想像到底發生在何處?這位想暗殺親王的朝鮮青年為什麼會選擇在異國的一座城市下手,而不在他熟悉的場域舉事呢?他應該是難以活命了,但他的最終地會在那裡呢?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合聘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海客談瀛洲》(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