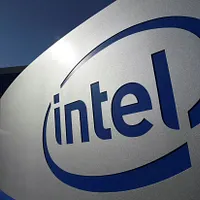引言:國賓未來的倒下,高雄失去的不只是飯店
2025年夏天,愛河畔的國賓大飯店面臨拆除作業。未來可能會出現許多人遠遠看著巨大的機具咬斷鋼筋、推倒牆面,心中湧上的不是「更新」的喜悅,而是失落與惆悵。這裡曾是無數高雄人的回憶:新人婚宴、跨年煙火、工商聚會、市民散步,國賓的身影早已內化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但在都市更新制度的邏輯下,國賓只是一塊土地與一棟老舊建築。它不再符合開發商的利益,法律沒有賦予它保存資格,結果就是「合法拆除」。市政府也能說,所有程序都合乎規範;建商則說,這是資產的最佳利用。但市民心裡清楚:國賓的消失,代表城市少了一段能讓世代共享的故事。
一、東京車站:差點消失的國家象徵
1914年啟用的東京車站,也曾面臨類似命運。二戰轟炸讓它毀損嚴重,戰後修復後的紅磚建築被嫌老舊,1970年代甚至有「拆掉、蓋新站」的聲音。按當時的經濟邏輯,推倒重建似乎最合理。但日本社會選擇了另一條路。
政府透過《文化財保護法》將其列為重要文化財,並投入數十年修復,恢復原貌。2007–2012年的百年修復計畫,投入超過500億日圓,讓東京車站重現戰前風采。許多人質疑「花這麼多錢值得嗎?」但今天的結果顯而易見:東京車站不僅是日本的象徵,更是觀光品牌,每年吸引數千萬人次,成為東京最受遊客喜愛的地標之一。
同樣是老舊建築,東京選擇保存與投資,國賓卻被判定「可以拆」。這一留一拆,背後是制度與觀念的不同。
二、制度的分水嶺:保存vs. 拆除
為什麼東京能留住車站,而高雄卻留不住國賓?關鍵在於制度。
日本自戰後即建立起《文化財保護法》,並在2000年代後更進一步將近代建築納入保存範疇。這讓戰後甚至昭和時期的建築,也能獲得文化資產地位,避免因「不夠古老」而被忽視。東京車站得以被保存,正是因為法律承認它的價值。
反觀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偏重清代與日治時期以前的建築,戰後地標多數缺乏定位。加上《都市更新條例》與《容積獎勵制度》強烈鼓勵拆除重建,《環評》又僅看污染與交通,不看文化與記憶。這些法律拼圖拼出來的現實,就是高雄國賓被「合法地」拆掉。
制度設計的不同,決定了建築的命運:在日本,老建築可以變身國家象徵;在臺灣,戰後建築卻只能在推土機下結束生命。
三、經濟帳與文化帳:誰真正划算?
拆除國賓的理由之一,是「經濟效益」。蓋摩天豪宅可以賣出高價,創造稅收,看似比維持一間老飯店更「划算」。但這種算盤其實短視。
相比之下,國賓變成豪宅,只能服務少數人。對整體城市而言,它帶來的只是短暫的房地產收益,卻失去長期的文化與經濟雙重效益。OECD的研究早已指出,保存專案的長期回報率比拆除重建高出2–3倍。高雄卻選擇了看似快速的開發,犧牲了能累積的公共資本。
高雄國賓與東京車站的對比,是一堂深刻的城市課。相似的建築命運,卻因制度與觀念不同而走向兩個結局:東京車站成為日本的象徵,國賓卻即將化為瓦礫。差別不在於經濟條件,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什麼才是城市真正的資產」。
四、世界的選擇:拆與留之間的第三條路
在全球許多城市,面對老舊建築,拆除並不是唯一選項。巴黎的奧賽火車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1970年代,它已不敷使用,幾乎被確定要拆除,幸好法國政府與文化界提出保存構想,最後將其改造為奧賽美術館。如今,它不僅是世界級文化地標,每年創造龐大的觀光收入,也成為巴黎的城市品牌。
倫敦的Bankside發電廠同樣在1980年代停用,最初被視為「都市廢墟」。但市府選擇保留主體結構,並與泰特美術館合作,打造出全球參觀人數最高的當代藝術館。這些例子都在說明:保存與活化能讓老建築不再是包袱,而是資產。城市的選擇,不只是「拆或不拆」,還有「如何重新賦予生命」。
五、亞洲的再生故事:城市如何與記憶共生
亞洲的案例更貼近臺灣的處境。東京車站已經是經典,但其他城市也展現了創新。
橫濱的紅磚倉庫曾經閒置,幾乎被遺忘。經過活化,如今成為文創基地與觀光熱點,結合藝文展演、市集與餐飲,帶來穩定的經濟收益。首爾的世運商場,一度被貼上「都市毒瘤」標籤,但市府透過政策與設計介入,將它轉型為青年創業園區與創新空間,重拾新的價值。新加坡富麗敦酒店更是經典:殖民時期的郵政總局,透過保存與改造,成為全球知名的五星級酒店品牌。
這些案例顯示,亞洲城市逐漸意識到,戰後建築不只是歷史符號,更能透過「保存+再生」成為經濟與文化雙贏的資產。相比之下,臺灣卻仍在「拆除最快、重建最有效率」的思維裡打轉。國賓的倒下,正是這種短視制度的縮影。
六、世代的選擇:我們要留給下一代什麼?
保存建築,從來不只是保留外觀,而是代際正義的實踐。當國賓被拆除,高雄的年輕人只能透過父母的照片想像那個曾經的愛河地標。這樣的結果,讓城市記憶斷層,下一代的歸屬感也隨之削弱。
柏林圍牆的保存,是一個有力的啟示。它本可以完全清除,但德國選擇保留部分牆體,讓年輕人能親眼看見歷史、理解過去。同樣地,首爾清溪川曾被高架道路覆蓋數十年,復原工程讓它重新流動,也讓新一代能在親身經驗中建立與城市的連結。這些案例都提醒我們:保存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讓未來世代能與城市對話。
若我們總是選擇拆除,下一代將繼承一座座沒有記憶的摩天樓。他們或許會住得更高、更現代,但是否還願意留在這座缺乏情感連結的城市?這是代際正義的真正考題。
七、臺灣的制度覺醒:避免下一個國賓倒下
國賓案的失落,凸顯出臺灣迫切需要制度改革。首先,《文化資產保存法》必須修訂,將戰後建築納入保護範疇,避免它們因「不夠古老」而被忽視。其次,都市更新與大型開發案應導入「文化影響評估(CIA)」,就像環評檢視污染一樣,文化價值也應成為必須考量的項目。
同時,政府應建立「保存+活化」的誘因,讓建商在更新計畫中能獲得支持,而不是被動面對「保存即成本」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應該設立市民論壇與青年席次,讓不同世代都能在決策過程中表達意見。
鹿特丹與哥本哈根的經驗顯示,當文化、永續與市民參與被納入制度,城市才能真正走向長遠發展。臺灣要避免下一個國賓倒下,就必須讓保存成為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依靠零星的抗議或臨時的情感呼籲。
國際與亞洲的案例反覆強調:保存不只是情感上的浪漫,而是能創造經濟效益、強化世代連結、提升城市品牌的資產。東京能留住車站,是因為制度與社會共識承認「記憶就是資本」;臺灣留不住國賓,則是因為我們仍把記憶當成可以犧牲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