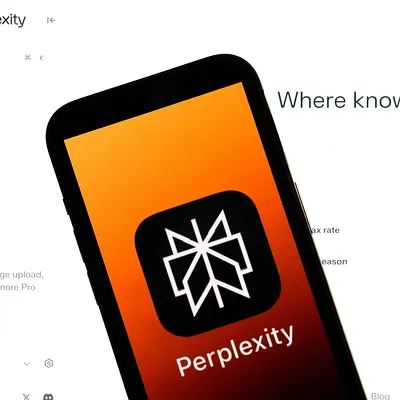8旬劉女士含辛茹苦照顧重殘癱瘓的兒子半世紀,民國112年新冠肆虐時自己染疫,終於心力交瘁,用紅包塞進兒子的嘴,讓他窒息而亡,近日被判刑兩年半。各界、包括法界同向賴總統請求,終獲難得的特赦,而且社會上同情劉女士的聲音更遠遠超過譴責。但是,那位可憐的劉女士仍在「悲傷中沉默不語,自覺做錯了事、自認有罪」。
一、個人主治醫療家祖父的過往
筆者是一位非常資深的神經科醫師,對劉女士痛楚的「自責」感同身受,因為30多年來也常覺自己逆倫「弒祖」:
那時台灣經濟和醫療品質剛開始起飛不久,醫療不普及、交通不便、沒有長照、沒有移工,社會普遍(甚至醫界)對失智認知不足、更沒有「緩和醫療、善終」等觀念。那年,家祖父年近94,大病沒有,但有嚴重的白內障、耳背…、住在無電梯的五樓,行動實在不便,智能漸漸地減退、時空有時錯亂,父執輩都70餘歲,也年老體弱、有心無力,孫輩忙於學業、工作,很難隨身照顧,祖父原是個飽讀詩書、勤寫毛筆字、愛朋友、愛生活的人,生活品質變得極差。最後筆者只好將他托付於鄰近我住宿舍一個新開張的私人養老院。沒想到入住不到兩天,鼻胃管脫落,那裡的看護自以為是、胡亂地插回,不計後果地灌食,老人嗆至昏迷,被急送至我服務的北榮急診室,經過氣管插管、抽除大量食物、供氧,幾小時後,恢復了大部分神智。怕他隨時會自行拔管,老人雙手被約束,他對著病床前身著白長袍的主治醫師--他的長孫怒目而視,掙扎、擊床,表示恨透了那根呼吸道插管,我評估很久,最後隨他願,親自拔了管、也解開他雙手的約束,老人隨後平靜下來,但很不幸,半小時之後,護理同事緊急通知正在隔間尋房的我「您祖父呼吸停止、血壓、神智…」,我立即趕到,不知什麼力量指使我,當下我請所有的醫、護離開,並撤出所有急救器悈藥品,我扣上房門,垂手站立、靜伴老人祥和離世。我們家族當下沒人深究原因。
後來很長一段時日,每次祭祖或想起老人時都深感不安,自知平日已不夠關懷他,更見死不救,懷疑自己做的到底「對不對」,甚至擔心他的兒子們知道後會如何地責備我、未來神明會如何懲罰我。這陰霾藏於心底數十年,只與1、2位手足淺淺談及,總希望獲得心理上些微的救贖、而不可得。
有時妄想,家祖企圖拔管或許是他「活得不耐煩了」,也可能是他向子孫表達愛、不願拖累也是老邁的兒子們;而採取消極處置的主治醫師--我,是愛他、不願他再吃苦,還是我較憐惜我的父執們,還是…、或是都有?總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幹了人神共憤的事、還是幹了所謂孝順的好事!
二、情之難解,訴之律法
在往後的職場生涯裡,常有患者在生死關鍵時刻,家屬會問我專業以外的意見,筆者會告訴他們我個人治療我祖父以及父執輩們陸續離世時我做決定時的體會:「出發點是『愛』,任何決定都是對的,否則,所有的決定都是錯」。
民國86年7月,幾位台北榮總同事、病友家屬和筆者成立「漸凍人協會」時,全台灣(甚至榮總)呼吸器嚴重不足,我首先呼籲台灣非要立即推廣「機構式呼吸治療中心」不可,否則無法長期(甚至緊急時)救助需要輔助呼吸的他們和其他神經疾病的患者。86年10月16日,在郝龍斌、沈富雄、林正則等委員協助下立法院通過,現在呼吸治療中心已多到近乎過度,應該幫助了不少有呼吸障礙、病危的人;後來,與一些患者深談,發現有些患者客觀條件不足,不願長期臥床、靠呼吸器維生,深怕影響家人太大,寧願選擇終止餘生,有些還具體實踐,自然往生。
鑒於個人「把死亡的自主權應該交還給病人自己」的體會,和臨床診療退化性神經肌肉疾病患者之所見,一本美國相關書藉「Good Final Exit」給了筆者靈感,首創「善終權」一詞,86年8月並與熱心於「安樂死」的社會人士徐子琁小姐開始在立法院遊說林正則委員推動「善終權的立法」,約兩三年後,89年5月23日敗於「緩和醫療條例草案」,據知情人士的透露原因,筆者感到寡不敵眾,雖敗猶榮;
其間,在89年1月9日受台大教授聯誼會之邀,演講「安樂死?尊嚴死?善終權!」,提出了本人「善終權之死」,與安樂死和尊嚴死的不同和優點,檯下有許多教授,還有數位宗教人士,後來該聯誼會還特地寄來感謝狀,稱許演講「內容豐富、精彩」;
89年6月5日又受台大法律系/研究所之邀演講,發表對協助患者實踐「善終權」的方式。原則上,就是把生命危急時,所有臨床可能發生的狀況(參考榮總醫療及急救處置手冊)和相對醫療可能處置的方式和分類,以及目地是使患者延命或是舒適,均詳細列表,預先與患者本人詳細說明,獲得患者授權、簽訂,而後「照表操作」,不但死者臨終可完全自主,且醫、病之間毫無窒礙(詳細內容刊載在於常春月刊於94年8月號)。筆者特別請教在場眾學者有無違法,他們沒有任何反對或覺得不妥的異見。
三、長照人倫悲歌的預防
醫學大大的進步,但台灣幾乎仍三不五十會出現照顧者殺人的新聞,依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統計,「2009年至今累計超過百起」,多數加害者是長期照顧配偶或子女的年老家屬,動機往往都是長期壓力(平均照顧十年以上)、疾病惡化、經濟困境和不忍對方吃苦(怕自己先走,無人接續照料)。過去這類悲劇,政府和媒體一向歸責於「長照資源不足」的老問題,雖然加上法律判刑(平均4年10個月),但人倫悲劇仍時有所聞。
筆者個人當年放棄對家祖父急救,長年以來內心時「悔」、時「悟」,加上長期照顧神經肌肉疾病患者,對相關議題非常關注,在此提出以下的建議:
1、醫師在「極力搶救病危患者」時,是否也加以考量家屬社、經、學等能力是否足以承接後續對失能失智者的長期照顧,若否,應敢於向家屬明說、無懼地建議放手,當然「法律也必須配合鬆綁」。54年前,當筆者還是實習醫師時,曾和一位老師急救一位家境很不好的患者,他開立的處方不是最有效的藥、而且劑量不足,事後對我的質疑,他說:如果這樣做違反醫德、有損陰德,我們醫師就承擔起來吧。這個教誨讓我感記在心。事實上如今我也年過古稀、直奔耄耋,早已交代家人,在我自己生命危急時,除非暫時性的,否則絕不能讓我長期臥床、失智失能;若能吃喝些就從口餵,除了導尿管(尿脹會痛苦),「所有的鼻胃管、氣管插、氣切、急救…都免談」。
(相關報導:
余祖慰觀點:為何國人長照保險投保率不高呢?
|
更多文章
)
2、台灣人口老年化海嘯已然來襲且快速加劇中,衛福部預估今年失能人口將逾91萬,相信其中有很多家庭的主要照顧者沒有能力面對長期的壓力和經濟困境,長照資源不足的紅燈早亮起,各級政府應即時「誠心」集思廣意,全力務實應對,否則源源不斷的會有被起訴、被判刑、求緩刑的人,特別是老人,情何以堪?
3、長期照顧失能,最需要的是人力、空間和財力,其中財力最是關鍵,愚見以為,其實有一個合情合理的財源:台灣因單身及無子女家庭增加,「孤獨死」後無人繼承的遺產逐年攀升,每年約1到6億元的資產,有時單筆高達上億、甚至接近3億,民國 98年至112年合計超過43.7億元,這些錢都「上繳國庫」,卻沒人過問「這筆鉅資後來的去向」?另外,還有數萬筆土地與房屋(價值預估將近千億)逾期登記,法院清償賸餘後,最終也全數也會「收歸國有」。筆者呼籲,「國家/政府」若無法律依據,無權占有這些年年都有的資金,說難聽點無疑就是腳尾錢,不但應該釋出補助長照,而且更該「專款專用」,讓孤獨往生者生前努力所得的積蓄照顧當下孤獨的甘苦人!
4、至於實際執行面(在宅式、機構式或家屬以工代宿互助「類機構」式、捐屋換顧等),應委請民間一些奉獻已有所成的社會賢達提供建議或參與,例如最先無條件照顧植物人的曹慶老先生(創辦創世基金會)、人稱「王聖人」照顧孤身失智患者的王建煊院長(創辦無子西瓜基金會/天使居)、慈濟基金會、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等等。
那麼,到底什麼是中華文化裡五福之一的「善終」?筆者89年在台大教授聯誼會演講中將之定義為-「往生者:不怨、不痛、不爛(褥瘡);家人:不憾、不亂、不散」,當時無人提出更好的詮釋。
(相關報導:
余祖慰觀點:為何國人長照保險投保率不高呢?
|
更多文章
)
綜上,衷心期盼「善終」成為權力,醫界、社會善心人士和朝野當權諸君,為劉女士們、更為任何人,敬請參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