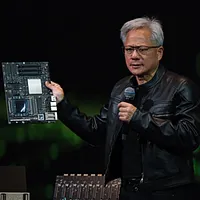川普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之後,我拿了兩三堂課專門講美國政治制度。我們討論了選舉人團制,討論了媒體宣布結果的方式,我還談到敗選者承認敗選的傳統。同學感覺都很清楚,就算他們有幸災樂禍,也沒有表現出來。
整體上,這些年輕人感覺不會特別自我感覺良好。每學期,我都會在開給大一的課上教《動物農莊》,出一份作業,請他們寫自己最認同的角色。最多人選的是「驢子」班傑明,他對新農莊抱持懷疑,但把想法放在心裡:
「我覺得,如果我跟另一邊的力量相差懸殊,那實在沒有以卵擊石的必要。當然,我還是很欽佩敢於反抗的人,只是我個人不會冒這個險。」
「中國有一句成語說得好,『禍從口出』,意思是一個人惹的禍都是口舌造成的。我們有兩隻眼睛,兩隻耳朵,兩雙手,但只有一張嘴,這就是要我們多看,多聽,多做,少說話。」
「我的性格缺陷和他的很像。他看穿了豬的統治的本質,但沒有反對拿破崙明目張膽的獨裁之舉。他不敢像雪球那樣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也不敢挑戰拿破崙……這是一種膽怯,或者是自私。就這一點,我跟他很像,我只關心我擺在心裡的那一小群人。」
繼班傑明之後,第二多人選的是「拳手」。歐威爾小說中,拳手是一匹勤奮工作、反應遲鈍的馬,總是聽從拿破崙的領導。小說近尾聲時,過度工作毀了拳手的健康,牠也被賣給收購老弱馬匹的商人,之後會把牠殺掉加工。評論者認為拳手是暗喻俄羅斯工人階級,他們支持在革命期間支持共產黨,而後付出痛苦代價。有些學生在這個悲劇角色身上看到自己:
「我也是個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經常人家告訴我什麼,我就信什麼,我都會不假思索完成別人交代的工作。要是我是農莊裡的動物,一定會相信雪球和拿破崙這些領袖的話……也許我會被拿破崙洗腦,最後變成拿破崙命令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的那種動物。最後,我會被拿破崙踢到一邊。」
同學們對自己可以非常坦誠,對於中國的體制也沒有多少幻想。這跟我在一九九○年代的經驗大不相同,當時班上同學都很天真青春。那時候,我得時刻提醒自己,我的年紀沒有比我的學生大多少。「一不小心就會笑他們荒謬的名字,或是笑他們純真的羞怯。」我在《江城》裡這麼寫著,「一不小心就會把他們當成出身純樸鄉間的、單純的年輕人。但這當然完全不是事實——四川鄉下並不單純,我的學生已經懂得我從未想像過的事情。」當時,學生看起來年輕是因為他們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現代中國的每一代人都是這樣。年輕人一次次身陷巨變的漩渦中,也許是戰爭的或革命的,也許是政治的或經濟的。
但川大同學有著老靈魂。他們曉得事情的道理,他們了解體制的缺點,也了解體制的好處。他們進入的,是他們的父母曾經工作過的環境——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穩定、繁榮的時間長度比大學生的記憶還要長。身為進入中年的老師,我的觀點也改變了:現在我得提醒自己,我的學生沒有感覺起來那麼老。像虹儀這樣的大二生寫起父母那一代人,寫起自己將來要承繼的社會時,是可以完全冷眼以對的: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
「我父母生在一九七○年代,我想他們現在算是中國的中下階級。他們有著堅定的愛國情操與冷漠的自私自利。他們堅定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方法不是誇讚中國政府,而是批評外國政府。他們拒用蘋果產品,不去日本旅遊,把川普斥為狂人與惡人。但他們很少熱情誇讚中國。他們見識過中國官場的腐敗與社會的不公義,對此束手無策,所以他們老是說,『事情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這代生長在網路世代的人,對於中國信仰與西方信仰之間的衝突感到不知所措,還有點沮喪。網路上都在宣傳自由與理性,課本裡都在宣傳愛國與共產主義。年輕人多半受前者吸引,但在考試、求職的時候,心裡要考慮的卻是後者,而且後者在中國實際上多半運作得比較好。」
疫情期間,想到黨和國家就很傷心 我在一年的最後一天,上了這個學期非虛構課的最後一堂課。我問同學一個問題:你覺得二○二○年這一年是好還是不好?
十二月上旬,學校再度對外關閉。天氣漸冷,中國也跟著經歷幾次新冠爆發,源頭多半是經過隔離的歸國公民。成都則是有一位老人家經手隔離設施附近遭到汙染的垃圾,由此拉出一條傳染鏈。第一起個案在十二月七日通報,接下來五天成都市篩檢超過二百萬居民。雖然從二月以來就沒有病例,而且成都全體只有一百四十三例,但城裡卻有一百四十一座採檢站,這個比例幾乎等於是從疫情大流行以來,每出現一起非境外有症狀感染個案,就設一處站點。十二月通報的社區傳染新病例也就十三起。
大學裡沒有人染疫。但舊體系回來了:保安監視著圍牆的破口,學生的臉又刷不開校門的閘門了。成都各地有少數針對性的封鎖,但我們社區與城裡大部分地方都維持正常。愛莉兒和娜塔莎的學校保持開放。疫情新起的這段時間,成都還開通了五條新的地鐵線。
我學生有將近七成回答是個好年。但他們還是有老靈魂——就算情況變好,他們還是難以理解體制的矛盾。非虛構課的文森寫道:
「待在家那一段時間,我注意到中國政治體制有太多問題,也開始思考怎麼樣解決問題——至少我可以為國家做些什麼。疫情期間,我讀到新聞說醫生犧牲奉獻、人們失去親人,還有其他令人難過的消息時,我有時真的對國家很失望。我很氣我們政府……當時我一想到黨跟國家就覺得很傷心。」
「但後來情況轉好,看到其他國家更糟的表現,我對中國和黨的看法也變了。雖然我知道中國還是有太多既有問題,但我也變得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比較先進,尤其是情勢危急時。」
李德威也說這年是個好年。Feetmat、Troadlop和其他鞋子品牌迎來歷年來最好的耶誕假期銷售額,而且相較於二○一九年,這年的整體收益增加了百分之十五。Pemily12賣得很好,李德威深信自家企業將來會涉足寵物美容商品,賣給美國人。
「跟人用的美容用品差不多。」他在我二○二一年初來訪的時候告訴我。他給我看一張狗用假睫毛的圖片。「我們還沒開始做,」他說,「但已經看到其他人在做這種產品。也許一兩年就會有很大市場。」
浙江的旗幟製造商金崗的這一年就比較困難。歐洲大型運動賽事閉門舉行,影響了他的生意。但美國首都一月六日的暴動發生後,川普旗幟的訂單激增。金崗寄了三張目前生產中最受歡迎的新設計圖片給我看:
每逢星期一,愛莉兒與娜塔莎會圍起少年先鋒隊領巾,別上金章,以「采采」與「柔柔」的身分上學。她們有時候會埋怨不能回科羅拉多玩,加上很想念家裡的貓咪穆爾西,現在是我們的租客在照顧。但那種日子感覺愈來愈遠。某天下午,兩姐妹在府河邊發現一隻小小的棄貓。她們把貓咪帶回家,取名叫尤里西斯,因為他也離家好遠。她們也按照中式做法,馬上給這隻貓一個小名叫尤尤。
這裡也真,那裡也真——這是最好的應對之道。我們在兩個家都掛起特定的家庭相片,重複的還有幾件宜家家具。在科羅拉多,我們家的黑色本田CR-V停在穀倉裡;這年秋天,我們買了另一輛黑色的本田CR-V在成都開。我們中國這輛本田是在武漢製造的,所以我們叫它是COVID車。連那座封城的生產線也過了個好年,本田表示在二○二○年,汽車銷售量比去年多了將近百分之五。開車去學校的話,我就把這輛COVID車停在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地下室裡。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牛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2000至2007年間曾擔 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本文選自作者最新作品《
別江 》(八旗文化)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牛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2000至2007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至2016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2019年舉家搬到中國四川,並於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授課。本文選自作者最新作品《別江》(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