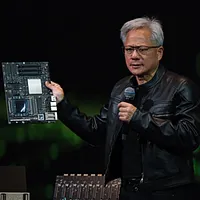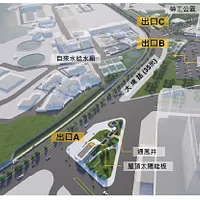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存在發現了一件事:偷竊不是犯罪,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天賦,也是一項被包裝成文明使命的行為。凡是落入它手中的一切,都會在一瞬間被追溯性地轉化為「合法財產」,土地、書籍、房屋、孩子、農作物、文物、檔案、人體器官、飯店毛巾,甚至連血統本身也不例外。沒有差別。唯一的標準只有兩個:東西存在,而它的主人不是正忙於死亡、流離失所、被困在檢查哨後,就是正睡在杜拜的飯店裡。
偷走血統(或者:一夜之間如何變成「古老民族」) 在談論房屋、書籍與孩子被偷走之前,我們必須先從最大的那場偷竊開始:對身份本身的偷竊。整個殖民計畫建立在一個簡單的說法上:「我們是古代族群的直接後裔,如今只是回到祖先的土地。」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浪漫的故事,動人的故事。
但這裡有一個微小的問題:多數建立這個體制的「新來者」,其實來自東歐,特別是阿什肯納茲族群。而歷史上大規模改宗的紀錄是清楚可查的:高加索地區的可薩人(西元八世紀)、改宗的希臘人與羅馬人,以及多個歐洲部族。
那麼基因研究呢?它顯示:今日的巴勒斯坦人,在基因連結上,與古代巴勒斯坦居民——包括古代猶太人——的關聯,反而比今日的猶太人口更為接近;而現代猶太族群本身,則是混合基因的結果。
但官方敘事怎麼做?它忽略事實,選擇神話。血統先被偷走,然後,一切其他的東西才陸續開始消失。
大型不動產竊盜(或:法律如何把竊盜變成「行政程序」) 在雅法、海法、采法特、盧德,事情一開始並不只是戰鬥,而是一場專業級的資產盤點。這間房子合適,這段樓梯是原裝大理石,這個陽台景觀良好,這只櫃子可以立刻搬走。居民在槍口下離開,一隊隊的定居者拖著輕便行李進來,住進連房間數量都還沒來得及數清的房子裡。一家靠坦克運作、而不是靠合約運作的超大型房地產公司,於是正式開張。
1950年3月,《缺席者財產法》生效,任何在1947年11月29日之後離開住所的人都被定義為「缺席者」,即便他仍然身處同一個政治實體之內。房屋、土地、銀行帳戶、家具與書籍,全數自動轉為國有。只要你為了躲避轟炸而逃命,你是缺席者;只要你戰時去鄰村探望親人,你是缺席者;只要你被武力驅逐後試圖回家,你仍然是缺席者。而你的財產,則被正式宣告為「被遺棄」。
歷史學家希拉・羅賓遜估算,超過一萬間商店、兩萬五千棟建築,以及約六成的肥沃農地因此被沒收。有些房子不是只被偷一次,而是被偷了兩次:第一次,屋主被趕走;第二次,這些房子被當作「合法財產」出售給新的定居者。
同一年,1950年7月,《回歸法》通過,賦予世界上任何猶太人——以及其第三代後裔——立即移民並自動取得國籍的權利。同一個年份,兩部法律同時存在:一部負責驅逐原住民並沒收其財產,另一部則引進新的定居者並將這些財產交到他們手中。正如一位分析者所說:「回歸法促成大規模移民與殖民;缺席者財產法則將巴勒斯坦人剝離其財產合法化,並阻止他們回家。這是一場集體替換。」
(相關報導:
安海正觀點:噢,羞恥啊,一切榮耀都屬於你
|
更多文章
)
到了1954年,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已住進「缺席者」的房屋裡。在1948至1953年間新建立的370個定居點中,有350個建在「缺席者」的土地上。這是一場雙重獲利的偷竊,連財務報表都會為它鼓掌。
七萬本書,尋找一座圖書館 軍隊進入住宅,開始系統性地收集書籍,將近七萬本。這是一場強制性的「捐贈行動」。書頁上仍留著那些家庭的名字,而那些庭,至今仍然保留著自己房門的鑰匙。書如今安靜地躺在耶路撒冷的書架上,被標註為一個溫柔的分類:「被遺棄的財產」。
荒謬的是,書的主人什麼也沒有留下,他們只是被趕走了。但如果我們公平一點想,也許是書自己選擇留下?也許它們認為耶路撒冷的圖書館比燃燒中的海法書架更安全?也許書本自己,也曾夢想過更好的生活。誰知道呢。
既然能偷孩子,為什麼還要只偷房子和書? 現在來到竊盜的巔峰之作。這是一場需要非凡膽量的竊盜,一場值得人類停下來凝視的竊盜。
在1948年至1954年間,介於一千到八千名兒童從葉門、米茲拉希與巴爾幹家庭中消失。其中多數來自葉門家庭,也就是說,在建體最初的六年間,每八個葉門孩子中,就有一個消失。至少一千,最多八千。六年之內,每八個孩子就少了一個。不是戰爭,不是天災,而是在一個「現代國家」裡,在「現代醫院」中,在「現代制度」的管理之下。
母親抱著健康的孩子走進醫院,護士把孩子帶走「檢查」,母親等待,幾個小時後,有人告訴她:「你的孩子死了。」沒有遺體,沒有死亡證明,沒有墳墓,只有那句冷靜的句子:「你的孩子死了,走吧。」
有些家庭被要求將孩子交給托兒所或醫院,「以獲得更好的照顧」。有些孩子被社工或護士強行帶走,送上救護車,被迫轉入這些機構。有些母親拒絕,她們尖叫,不相信,於是孩子偶爾會被送回來,伴隨一句尷尬的道歉:「對不起,搞錯了。」搞錯?
加薩走廊南部城市汗尤尼斯,巴勒斯坦民眾排隊領取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發放的食物。(美聯社)
1950年代的證據顯示,政府官員、法官、立法者與醫院職員曾公開談論過綁架兒童這件事。公眾也許不知情,但權力機構是確實知道的。一些孩子後來出現在富裕的阿什肯納茲家庭裡,在特拉維夫、在耶路撒冷、在美國。原本沒有孩子的家庭,忽然獲得了「被安排」的孩子。深色皮膚的孩子,出現在白人家庭之中。
吉爾・格龍鮑姆四十年來一直以為自己富裕的養父母、納粹倖存者,就是他的親生父母,直到某次偶然,他才發現真相。他真正的父母,是貧窮的突尼西亞移民,他們當年只被告知一句話:「你的孩子出生時就死了。」沒有遺體,不准看墳墓,只有那句重複的命令:「回去吧。」
為什麼?因為葉門人被看作是「原始的」、「落後的」、「沒有能力好好撫養孩子的人」,而米茲拉希家庭被當作「壞人、原始人、注定失敗的案例」。這被稱作一場「拯救行動」——把孩子從他們的父母身邊「拯救」出來。
但那些被宣告死亡的孩子,後來給出了另一個答案。十八年後,一些家庭開始收到為「已死亡的孩子」寄來的徵兵通知。一位母親被告知孩子在1950年死了,但在1968年卻收到一封信:「請你的兒子前來報到服役。」錯誤?行政疏失?不,這是證據。
(相關報導:
安海正觀點:噢,羞恥啊,一切榮耀都屬於你
|
更多文章
)
七十年間,四個調查委員會得出的結論一致:多數孩子死亡了。但從未解釋,為什麼沒有遺體、沒有正確死亡證明、沒有墓碑,卻會出現徵兵通知。2018年,18個家庭獲准開啟所謂的墓穴,只有一個案例與真實身份相符。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將「孩子」視為可被重新分配資源的現代國家——像家具一樣,只是多了一顆心跳。
連農作物也有它的份 在約旦河西岸,橄欖季不是收成的季節,而是追逐的季節。農民抵達土地時,卻發現果實在尚未成熟前就被摘走了,或者橄欖樹被連根拔起。採收者是持槍的定居者,而軍隊則在一旁維持秩序,彷彿正在護航一場慈善收割節。
本地人權組織稱之為「在軍事保護下進行的有組織偷竊」。這個形容太溫和了。有些農民試圖回到自己的土地,卻被阻止,理由是:「此區為軍事封鎖區。」為什麼封鎖?好讓竊賊能安心工作。
在北部,連牲畜也被偷走了,山羊、乳牛,甚至連雞也不放過。一支擁有匿蹤戰機與衛星的軍隊,正在偷雞。極端高科技與原始的道德飢餓,在這裡同時存在。
偷竊人體器官(或:人如何被變成「零件」) 九〇年代,首席法醫公開承認,曾從遺體取走角膜、皮膚與骨骼作為醫學研究材料,未經任何同意。死人不會簽署同意書。到了2024年,加薩的家庭接回孩子的遺骸,卻發現沒有器官,空蕩的胸腔,消失的內臟。彷彿有一座工廠在夜裡運作,夜裡掏空身體,白天送回屍體。人,被轉換為可被採收的資源。
戰場上的偷竊(或:軍事購物) 士兵在民宅內自拍,手裡拿著黃金、手錶、電子設備,還有女性內衣。Telegram 上充滿記錄這場「購物」的影像。偷、拍、上傳,成為現代偷竊的標準流程。一名士兵舉著金盒說是要給母親,一名士兵穿上從賈巴利亞偷來的婚紗。雞與山羊沒有倖免。一名農民回到自己的畜棚,發現裡面完全空了。軍隊,正在偷雞。讓我們停一下。一支軍隊,在偷雞。
杜拜飯店裡的「旅遊式偷竊」(或:當偷竊變成家庭嗜好) 2020年12月,直航開通一個月後,杜拜的飯店開始出現奇怪的現象:毛巾、茶包、咖啡包、燈具、熱水壺、義式咖啡機開始從房間裡消失。行李檢查成為標準程序。一戶帶著孩子的家庭準備退房時被要求打開行李箱,裡面裝滿冰袋、衣架與洗臉毛巾。在被告知將報警後,他們才歸還物品並道歉。
一名商人說,每次抵達飯店,都能看到旅客在大廳被檢查行李。一名評論員冷冷提醒:當你放棄房間裡的物品時,下一步,也許就是土地。
偷走文化(或:當連食物都被偷) 巴勒斯坦文物被重新命名,陶罐、錢幣、馬賽克重新被標註為「古代文物」。文物先被偷走,歷史隨後被偷走。食物也未能倖免。鷹嘴豆泥、炸豆丸子、馬克盧巴、馬斯漢、庫納法,忽然成了「傳統料理」。在紐約的餐廳裡,馬斯漢被稱為正宗配方,卻忘了它來自納布盧斯。
刺繡改了名字,檔案被一整輛卡車從貝魯特載走。沒有司法文件,沒有收據,沒有羞愧。在倫敦的一場正式活動中,前總統魯文・里夫林親口透露,伊麗莎白女王始終拒絕在白金漢宮接見他們的官員,除非是在正式的國際外交場合,因為在她眼中,他們「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的孩子」。連女王都知道。
加薩中部迪爾巴拉(Deir al-Balah),一名受傷男孩在阿克薩醫院為一名死者痛哭。該男子死於以軍對一家木工廠與咖啡館的空襲,遺體被送入醫院。(美聯社)
結語:給旅人的忠告 如果有一天你必須與它的代表握手,不要只檢查你的手指。你放手之後,可能會發現思想縮小了,記憶少了一段,血統忽然變得可疑,行李變輕了,地圖變形了,醫院裡的孩子「突然去世」,飯店裡的燈消失了,祖父的墳墓空了。與這個實體在一起,失去的不是口袋,而是你周圍的世界、你的歷史、你的孩子、你的名字。
這不是幻想,不是誇張,也不是陰謀論。這些是文件,是供詞,是調查,是母親們抱著被宣告死亡孩子的照片,因為她們知道,那些孩子在某個地方還活著。這正是當一個實體建立在「只要我想要,一切都屬於我」這個念頭之上時,世界會變成的樣子。而世界,正忙著看向另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