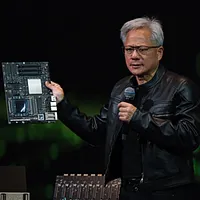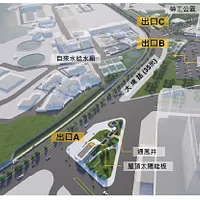所以應該不是真的故事,儘管我們知道,酷刑自古有之,人們對雙腳做過諸多更殘忍的事(商代甲骨文,圖像的存留很多剁腳的證據),但只是買雙鞋,應該不至於這麼傻,這麼背反生物本能吧。可也難說,這類事我愈活愈沒信心,人的獨特演化,好的壞的可以做出很多違反生物本能的事,愚蠢是其中極醒目的一種,那種無須刻意預判、光憑生物本能都不至於犯下的愚行,也因此,許多未來之事變得難以預見、斷言。困難不因為人可能太聰明太富創造力,因為聰明是有線索的,其行動是合理的,聰明是人迅速的、提前的掌握某個隱藏的因果;真正困難的是人笨,笨可以完全沒有邏輯沒有因果,突如其來,連當事人都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能說笨是唯一理由,單子也似攻不破的堅決理由。笨到沒底線,就等於不可測,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
我們這一代已老去之人,倒是對「削足適履」這個說得太誇張的成語很有感覺,應該是苦澀的,但時移事往在太長的時間裡反倒已變得甘醇的童年記憶,和食物的醃製發酵有點相似。那時候人不能浪費,人浪費是近百年乃至於這幾十年的事。童鞋、童衣尤其是很困擾的事,總是一季、一年就不能穿了,所以兄終弟及,不是帝王之位,而是制服球鞋。鞋子最麻煩,因為無法修改,所以,買鞋從沒有「適履」這回事,得買大一兩號的以為預備,塞團布塞團報紙就行了。
亞金.奧萊朱旺,極可能是NBA史上技藝最全能的絕世中鋒,尤其低位單打步法,夢的搖晃者,但這雙精妙無匹的腳,我早年讀他自傳,奧萊朱旺說,他在奈及利亞打球時,球鞋都是「撿」的,教練弄來一整卡車西方世界捐來的舊球鞋,得自己設法配對。七呎非比尋常身高,於是他從沒找到過合腳的、夠大的鞋。日後,他去了美國休士頓大學,此生第一次穿到全新的、剛剛好大小的、功學設計的專業籃球鞋,奧萊朱旺講,原來穿球鞋打球是這麼舒服的一件事。球鞋似乎是一直禁錮他雙腳的鐵鍊,這一掙斷,什麼都擋不了他了,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人們直接叫他dream,「大夢」,以夢為名。NBA天空,喬丹是神,奧萊朱旺是夢。
但這回再面對削足適履這四字,我是笑出聲音來著,事情發生在家裡,搞笑擔當是朱天心,卻意外成為一個文學話題。
幾十年來家裡一直有貓,也幾乎沒斷過那種被流浪母貓拋下來的仔貓。有朋友稍嫌豪放的抱起小貓,擔心小貓不舒服的朱天心出口制止:「不對不對,不是這樣,你要像抱小老虎那樣抱。」
這是什麼?是說,我要用一種我從沒做過的事,來理解來更正我還算做過的事,以未知來說明已知,這是什麼操作?
說來,抱小老虎,這還真是一堆人的夢想之事。波赫士認為老虎是全世界最美麗的生物,就因為這樣,他出言責怪他很喜歡的吉卜林,《叢林之書》裡,怎麼可以讓老虎當歹角呢?
(相關報導:
屠龍之技:唐諾《穿石》選文(1)
|
更多文章
)
比喻,形態上是座橋梁,我們用它來通往未知事物的世界,仔細點想,這好像還是唯一通道。差別只在,有時我們比喻的很明顯,有時很隱晦看不出來我們這是比喻而已(文字只是隱喻,只一個字的動詞,往往就是比喻,比方乒乓球場上,我們用「擰」來說桌面上的反手拉球,用「劈」來說下旋送球)。面對廣大的處處未知世界,我們的已知是唯一倚仗,像自己身上發出的微弱之光(我這是什麼個比喻,但能懂的,不是嗎?),難以立刻及遠一下揭開全部幽黯,但是一步照亮一步的,辛苦但實在。宮崎駿沒那麼成功的《魔法公主》影片裡,有很類似但比較美麗的描繪,那位隱喻般被人粗暴獵殺的森林之神,每走一步,腳掌下土地便開出花朵來。
但倒過來以未知揭示已知?朱天心無意間鑿出這個缺口,大家一陣搜尋,還真是,我們可能得認輸承認,最起碼在文字書寫世界裡,更經常也更讓人觸目一驚的,確實是「你要像抱小老虎」這種的。
比方卡爾維諾也詫笑過這個。義大利俗語形容劇痛,用了箭矢穿肉透骨的生動意象如說削足適履,卡爾維諾說,「這好像說,所有義大利人都有被利箭射中臀部的悲慘經驗。」
像愛用最強烈字眼來嚇讀者吸住讀者的狄更斯,張口生花已屆臨騙子程度的吉卜林,往死裡去往惡之深淵直去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耽溺於美已像是變態老人的川端康成(曾用水蛭來說女性嘴唇之美),或好像眼前世界萬物俱靈直通上古的賈西亞.馬奎茲云云,族繁不及備載。
但我還是最推薦杜牧的這句七言詩行:「落花猶似墜樓人」,反差高低太大,都要耳鳴了—同樣,落花尋常之事,見過千朵萬朵不計其數,尤其日本四月櫻花吹雪季節;但我這一生活六十五歲了,還真的從沒看到過任一個墜樓之人。可也這樣,那個無可抗拒的重力加速度沒了,人輕盈了,我們大致猜到杜牧心裡想的是東晉的絕世美女綠珠,然後那個霸氣敲碎名貴珊瑚的石崇,那個又誇富享樂卻又要棄絕這繁華如夢的奇異歷史時刻,人又要遠去卻又依依不捨的時代。
所以,我們可能得重新理解「經驗」是什麼,它可能不知不覺被窄化,窄化到人不該成為人,人應該仍是生物界的馴服一員。
最好不要把經驗只想成是親身經歷,這是實證主義的謬誤,也是左翼唯物論者常犯的錯。六尺之軀、七十人壽,人能親身經歷的東西其實很少,少到會嚇你一跳,也千萬別再相信所謂「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這類胡話,人異於其他物種幾希,其中之一便是各種工具的發明和使用(很長時間甚至成了人的定義),突破了生物限制,延伸了人的身體,延伸到人摸不到、看不到、走不到、甚至純生物性感官有時而窮難以捕捉的東西及其所在。所以波赫士這麼講:「在人類使用的各種工具中,最令人驚歎的無疑是書籍,其他工具都是人體的延伸。顯微鏡、望遠鏡是眼睛的延伸,電話是嗓音的延伸,但書籍是另一回事:書籍是記憶和想像的延伸。」
由此,波赫士說,閱讀就是「經驗」,跟你走上街頭、邂逅了某位女士云云沒什麼不一樣,都是作用於人身血肉的可感之事。當然,這中間得有一個「轉譯」的過程,但這並不困難,也絕對不是一個無法彌補的致命缺憾。這小小缺憾同樣一直被誇大,誇大到不知是何居心的地步。我有時會想,書不是非讀不可,人不讀書也過得了一生,這是自主之事,並不必找這種理由。
把文字符號轉為實體經驗真的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基本上只需要時間,需要耐心而已,你甚至不必特別做什麼,交付時間即可。只因為人的理解總延遲發生,通常不在當下,以已知來消化未知吸收未知,是一個過程,最近我重新把林芙美子小說仔細讀過,發現她總是這麼寫,安南的異國往事,回到東京才一件一件明白過來;白天的死亡,人的哀慟要到半夜才真正襲來,在激烈的雨聲中,爆發成生理性的腹痛腹瀉云云。我們任誰都是這樣,事後之明,事後才明,所以也總是帶點懊悔之感。野貓般闖進世界、異常生命經歷最多如不斷被懲罰的林芙美子比我們更清楚人是這樣,也熟成的化為一個小說書寫技法。
閱讀的必要轉譯,文字符號是一個問題加重其難度,但更根柢的,我以為就是「濃度」的問題,閱讀必然性的暫時消化不良—文字書寫(不包括眾多亂寫的),總是經由書寫者精純程度不一提煉過的。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那些駭人的事一件一件個別來看,其實並不會驚嚇我們,並不怎麼超出我們的認知,這哪件我們真不知道、沒在新聞報導裡看過呢?但該死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讓我們擠在那幾天裡,甚至在同一個夜晚發生,真正讓我們「破防」的是這個,超出了我們心智情感的承受力以及我們保衛性的遺忘和冷漠,我們猝不及防,記憶一個一個被叫回來叫出來;甚至,量變帶來質變,如此高密度的罪惡覆蓋了我們原有的世界圖像,覆蓋了我們心中人的基本形貌,我們不得不重新想,也許真正可怕的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