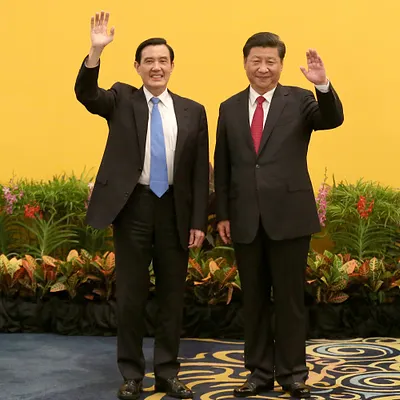近年來,城市保存成為全球流行語。廢棄的工廠被改建成展覽館、老鐵道變成觀光步道、倉庫被改造成文創基地。巴黎的奧賽美術館、倫敦的泰特現代、紐約的High Line、台北的華山與松菸,城市的歷史被包裝、陳列、導覽。這些空間讓人們以為「歷史正在被保存」,然而在展示的過程中,城市也悄然成為一座巨大的博物館。
博物館化(museumification)這個詞最早出現在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的著作裡。他提醒我們:「現代社會在保存中毀滅,在展示中遺忘。」當我們將時間封存在玻璃櫃裡,歷史不再流動,而被定格為消費的背景。文化保存變成一種視覺表演,記憶成為「可被拍照」的物件,而非「能被生活」的經驗。
以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為例,這裡曾是貨櫃堆疊、海風混雜柴油味的老港區,如今卻是週末打卡熱點。牆上的鏽蝕斑駁被刻意保留,燈光設計成「工業懷舊風」。遊客拍照、商家販售紀念品、地方政府宣傳「港都再生」。城市的記憶被精緻化、無害化、觀光化。我們懷念的不是港口,而是懷舊的感覺本身。
保存與展示之間,潛藏著一個根本的矛盾:當一座城市需要用博物館來證明它的歷史,它或許已失去了活著的記憶。
過去,城市由規劃師設計;現在,城市由品牌經營。政府以「文化再生」為名吸引資金,企業以「公益」之姿包裝投資,文創園區、老屋再生、藝文特區,這些詞語看似溫柔,實際上卻是空間治理的另一種語言。
紐約High Line的故事最能說明這種轉變。那原是一段廢棄高架鐵道,在社區運動推動下被改造成高架步道,並成功吸引上千萬人造訪。High Line成為「文化成功典範」,卻也帶來地價暴漲、原居民遷出、社區階級化。文化成為資本最柔軟的推手。
東京的「上野公園博物館帶」、首爾的「東大門設計廣場」,也都在重複同樣的劇本,當城市以展覽館思維運作,居民就變成展示的一部分。
臺灣的版本更熟悉:華山、松菸、駁二、鐵道園區……一座座「文化再生地」誕生,卻很少有人問:那些曾在此工作的勞工去哪了?那些被拆遷的老社區如何被記錄?
策展城市的邏輯是:要有故事,但不能太複雜;要有歷史,但不能太痛苦。於是我們看到的是「文青式懷舊」:老磚牆搭配手沖咖啡、老廠房賣設計商品。文化被消費、歷史被美化。城市看似被再生,其實只是被包裝成可售的形象。
博物館化城市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不只是保存,更是篩選。在展示中,總有人被記得,也總有人被遺忘。
在臺灣,這個問題同樣存在。白色恐怖、二二八、公娼制度、原住民遷村、移工勞動史,這些議題或被簡化成官方導覽的一頁,或根本無從展示。文化資產法的框架裡,「可被保存」的,是建築、雕塑、物件,但「難以保存」的,是生活、語言與情感。
當城市被設計成文化展場,政治的選擇就藏在每一個看似中性的展覽文案裡。誰能進入玻璃櫃、誰被留在門外,決定了城市記憶的方向,也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歷史」。
以高雄為例,愛河兩岸的再生工程把「老城市」打造成觀光地景,卻幾乎看不見工人與居民的故事。曾經載滿貨物的港邊,如今只有燈光秀與音樂節。歷史被美化成風景,失去了摩擦與爭議。
從老屋咖啡到復古旅店、從老字號商標到手作集市,城市似乎在與時間和解,但實際上是在消費時間。義大利社會學者David Harvey稱這種現象為「資本的時間修辭」:當代城市用懷舊來製造安全感,讓人們在消費中獲得「歷史參與感」。
香港中環的PMQ原為警察宿舍,如今成為文創商場;首爾的北村韓屋村成了觀光景點,居民被迫搬遷,只剩外地旅客拍照留念;台南藍晒圖文創園區的牆面上仍保留老屋輪廓,卻早已不再屬於原本的社區。
懷舊的政治在於,它讓人相信歷史可被擁有,卻忽略歷史本是流動的。「回到過去」的幻覺,其實是讓人停留在安全的想像中。城市的懷舊,不是回憶,而是設計。
當保存成為美學,歷史被淨化成可被觀賞的物件。人們感動於修復的磚牆,卻不再問那面牆曾聽過誰的聲音。博物館化的城市,在保存中失去了變化的能力。
要讓城市從展示回到生活,首先要學會「去博物館化」(De-museumification)。這並不意味要拆掉博物館,而是讓城市從「被觀看」變回「能呼吸」。
阿姆斯特丹是典型的例子。這座被登錄為世界遺產的城市,長期面臨觀光擁擠與地方居民流失問題。近年市府啟動「生活遺產計畫(Living Heritage Program)」:鼓勵老屋由在地住戶經營小店或工坊,禁止純商業出租,並要求保留生活功能。市政宣告:「我們不再把老城當成景點,而是當成家。」
在哥本哈根,城市設計者採取「使用即保存(Use it to preserve it)」原則。老建築不一定要變成展館,而可以繼續成為學校、工坊、住宅。他們認為:「最好的保存,是讓建築繼續被用。」
臺灣也出現一些類似轉向。嘉義「檜意森活村」由地方文史團體與市府合作營運,除了觀光,更設有居民公共廚房與在地工藝教室;花蓮「舊酒廠再生」計畫讓青年團隊共同經營,以社區為主體決定展覽與活動內容。
這些例子提醒我們:記憶不是玻璃櫃裡的標本,而是街坊日常的延續。當人重新進入空間,歷史才重新流動。
真正的文化保存,必須讓「被展示者」成為「敘事者」。
英國利物浦的「社區博物館(Museum of Liverpool Life)」則讓居民擔任策展人與導覽員。展出的不是帝國歷史,而是碼頭工人、音樂人、移民家庭的生活。策展權下放,使歷史重新「多聲」。
臺灣的鹽水蜂炮文化保存計畫,也嘗試這樣的方向。地方居民參與展覽設計,主題從「煙火技術」轉向「社區精神」。導覽手冊中不再只是祭典流程,而有居民手寫的故事與照片。
這種「社區策展(Community Curatorship)」的精神在於:保存不再由上而下定義,而由社區共同詮釋。歷史成為一場對話,而非審查。
文化若要活著,就必須被講述。被展示的城市是靜態的;被講述的城市,才有呼吸。
當科技滲入生活,記憶的形式也在改變。我們不再只在現場參觀博物館,而是在雲端參與它。
Google Arts & Culture、線上展覽、AR城市導覽,使歷史可以被隨時調閱、被任意重組。城市記憶的保存,從地理位置轉為資料雲端。
這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數位記憶雖可延續資訊,卻可能稀釋脈絡。誰在管理資料庫?誰能上傳、誰能刪除?這些都涉及「記憶的治理」。
歐盟推動「開放文化資料計畫(Open Cultural Data)」:要求公共博物館資料庫免費開放,並允許公民再利用。韓國釜山推出「城市記憶平台」,收集居民老照片、口述歷史、地圖標記,形成線上「社區博物館」。日本京都也建立「數位町家計畫」,以3D掃描保存老屋結構,同時開放建築師與學生下載學習。
臺灣雖有「文化資產地圖」與「文化銀行」等平台,但資料仍偏向官方與建築物導向,缺乏居民參與。若能結合社區故事、在地影像與群眾共筆,就能讓「資料」轉化為「記憶的公共財」。
數位化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民主化。當每個人都能上傳自己的城市記憶,博物館不再是封閉建築,而成為共享網絡。
記憶不是無限的。城市若只一味保存,終將被自己的重量壓垮。因此,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記得,也包括「遺忘的權利」。
哲學家保羅.李科說:「記憶的倫理,在於能原諒也能記得。」真正成熟的城市,懂得選擇哪些應留存、哪些該放下。
柏林是典型例子。牆倒塌後,政府沒有全部拆除,而保留部分斷裂遺跡,讓它成為反省與對話的場所。人們在斷牆前拍照、閱讀、沉默。那不是懷舊,而是一種公共療癒。
日本廣島和平紀念館也採取「非和諧的保存」策略:保留部分被炸毀的牆體,讓創傷可被看見而非被遮掩。
臺灣若要真正面對歷史,也必須走向「多重記憶」的路徑。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園區可以與原住民口述史並存;老社區的重建可以納入移工的勞動故事;文化政策不該只追求修復外觀,而應修復關係。
記憶不是一場展覽,而是一種對話的持續。當我們允許城市有不同版本的歷史,民主就不再只是投票的程序,而是共存的實踐。
若說「博物館化」是20世紀城市的趨勢,那麼「共創化(Co-creation)」應是21世紀的對策。
國際間已有新實驗:巴黎啟動「Participatory Heritage Program」,讓居民可投票決定文化預算去向;芬蘭赫爾辛基推行「共同策展城市(Co-Curated City)」概念,由市民組織、非營利團體與建築師共擬歷史建物再利用計畫。
臺灣也有潛在條件。地方文化館、社區大學、文化協會正逐漸形成公民網絡。若能建立「文化治理平台」,讓公部門提供資料、學界提供研究、居民提供故事,城市的記憶便能在合作中重生。
這種共創,不只是文化政策的創新,更是民主的深化。它讓城市從「被管理的對象」變成「能自述的主體」。
在博物館化的浪潮裡,我們學會了保存,卻忘了生活。我們記得牆、忘了人;記得地景、忘了聲音。
但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靜止,而在於流動。真正的保存,是讓時間繼續發生。
或許,城市應該像一本被不斷書寫的筆記本,有舊頁,也有新頁;有被擦去的痕跡,也有再書寫的勇氣。
當高雄的港口重新迎來居民散步、當台南的巷弄再聽見廚房聲、當巴黎的街頭藝術家在舊牆上重畫壁畫,那不只是「文化再生」,而是城市重新學會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