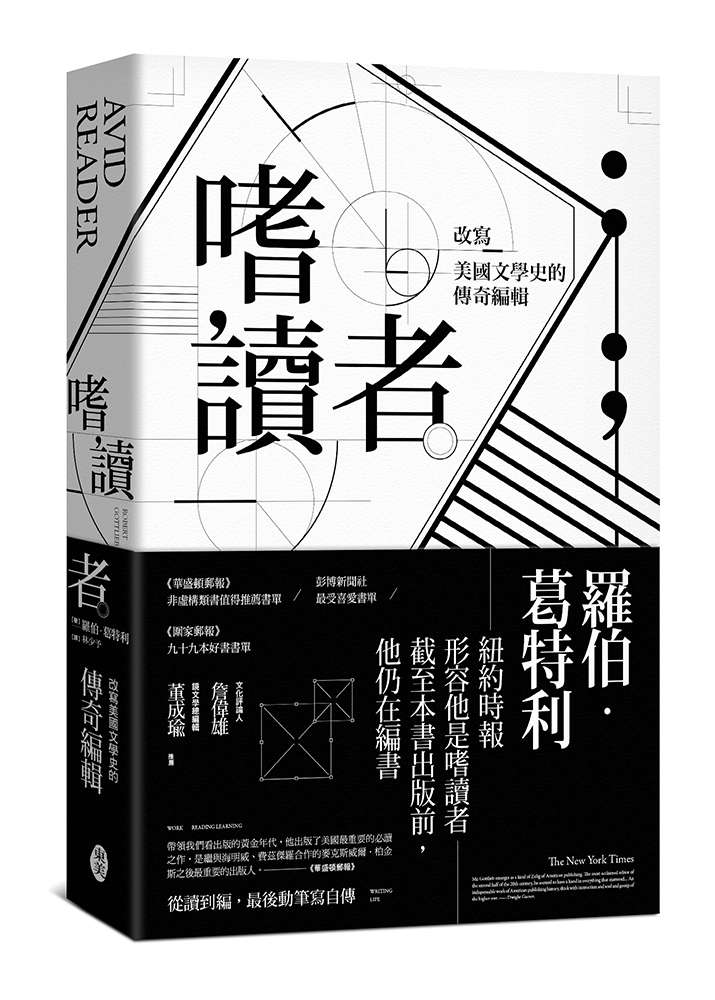寫作,是它找上我的。而且是偷偷地摸上我。我不像很多編輯,我一直對寫作沒有興趣;甚至更糟,其實我一點也不想當作家。我是說話型、不是打字型的動物。雖然我總是親自打寫信件(我覺得由秘書聽打,做作又沒有人情味。)手寫就更不可能了,我的手寫字潦草到往往自己都認不出來。
我必須寫的時候,比如說大學作業。就算過關、甚至拿了不錯的成績,但每次都是急就章、心不甘情不願地交差了事。寫作對我來說,就是太難;表達想法(假設真有想法)對我來說,就是太吃力。就像學鋼琴或心理分析一樣,寫作是痛苦追尋真理的過程。我在吐桑市唸七年級那年,我爸寫了封信給我(半世紀後我才看到。)他在信裡評論我寫給他的信(我不常寫信給他。)他說,有些人寫作是為了傳達嚴肅的事情、說明事實和分享理念;另一些人則用花言巧語迷惑人心或迴避事實。「你屬於第二種。」他宣佈我有罪,我也接受判決。另一方面,從事出版業必須撰寫大量書衣文案和廣告,懂得花言巧語還到不了十八層地獄。古往今來也只有尼娜有本事把文案變成藝術。
多年以來,我偶爾會寫一些文章,唯一有點分量的是一篇刊登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的長文。那時是一九六三年,我花了一整個暑假消化、思考廿(大)冊的《審讀》(Scrutiny)的心得。《審讀》是李維斯博士辦的期刊,是我大學時代的聖經。但鞭策我完成這個累死人的任務的原因,不是我欠《審讀》錢,也不是我的知性好奇心作祟,而是我拿不出一百元,卻非常想要擁有一整套期刊。卅五年後,我竟然再度陷入同樣的焦慮。
第二次焦慮的來源,其實是對我生命至關重要又讓我無法自拔的題目:「紐約市立芭蕾舞團」。格雷登.卡特(Graydon Carter)請我為《浮華世界》寫一篇舞團五十年的歷史,以及我與舞團關係的文章(我與舞團有很深的淵源。)對我來說,這是最大的挑戰,因為賭注太高了。要把這篇文章寫得對寫得好,似乎不可能。但我也知道,我是唯一有兩種「舞團」經驗的人:我看他們表演看了半世紀,我也深知舞團內幕。畢竟,我在巴蘭欽─柯斯坦的小圈圈裡打滾了那麼多年。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文章如何架構,接著出現的是要訪問、要讀資料的恐慌。終於完成了,我寫了一萬五千字?還是兩萬字?一個字沒刪。道格.斯圖姆夫(Doug Stumpf)的編輯功夫非常精緻。接著,他們要我幫忙找插圖。一篇關於芭蕾舞的文章,沒插圖不行。「舞團」那些人似乎挺滿意結果。但我寫的時候,可恨死了這任務。最恐怖的是,我一度固執地拒絕坐到打字機前面,甚至可以拒絕好幾天,但同時悔恨自己為何要負隅頑抗。唯一讓我滿意的是我終於完成這個艱難任務。還有,朋友的稱讚。 (相關報導: 地表最狂「維基人」就是他!13年新增3萬1千筆原創條目、編輯次數超過250萬 | 更多文章 )

在那篇文章折磨我的那幾個月,《紐約觀察家》報找上我寫書評,刊登在亞當.貝格利(Adam Begley)主編、生動有趣的書評版。事實上,找我寫書評的人就是亞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巴黎,我至交好友戴安.強生辦的晚宴上),他代表《觀察家報》總編輯彼得.卡普蘭(Peter Kaplan)在一個場合講話。卡普蘭是創意驚人又異乎尋常的編輯。卡普蘭就是想要我替他們寫稿,原因不明(我們到現在沒見過面。幾年後,亞當透露,彼得擔心如果他和我認識了,我可能會「接管他的腦袋」。他也許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我確定不懂:接管別人的腦袋又不是我的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