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的意義的改變,這本身不必然是件壞事。顯然地,特克的憂慮來自於她從一種浪漫懷舊的立場想像人自身。例如,在談到與機器人的互動關係時,她指出,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變化,是過去人們重視的人所獨有的那種情緒、情感性的「浪漫反應」,在如今這個機器人時代中,一切都是資訊至上。過去那專屬於人的「神聖」特質,如今已不再那麼重要。又或者,她在談到社交機器人作為伴侶逐漸成真的未來,也認為這是一種關係的簡化、貶低,在其中人喪失了學習進入並維持複雜關係的能力。因為機器人在她看來只是一種「自體客體」(selfobjects),只是個人需求、脆弱內在的投射,缺乏真正異己主體的反應能力。
特克的悲觀、憂慮當然不全是杞人憂天。無論何時,我們確實都需要警醒科技帶來的化約作用。但是,晚近諸多關於賽伯格與後人類處境的討論也顯示,我們仍然可以積極地看待、思索人與科技物歷經的這一親密轉換。一方面,行動裝置、社群媒體的永恆連結,不只有導致關係的化約、人的物化。如果從賽伯格的角度來看,人與行動裝置的親密結合作為一種延伸認知系統,我們確實有了跨越時空藩籬看見、聽到並共同感受的可能。進而,這種共同感受、回應的情緒,雖然不同於傳統社群紐帶,卻也開啟了共同生活的另類選擇。換言之,套用技術哲學家Don Ihde的說法,科技所帶來的影響始終都有著擴增與化約兩個正反並存的面向。我們需要警覺特克那令人不安的對稱,但也仍需積極地探問如何與科技更好地共生下去。
另一方面,對於人與科技物親密關係的反省,也不必然要從對人的懷舊出發。特別是當我們從Donna Haraway的賽伯格隱喻來看,人與科技物的親密關係反而能夠讓我們進一步反思「界線」的問題。這裡所謂的界線問題,指的是在過去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下,「人」一直被是為獨特的主體。就如同有一條不可踰越的線,區分出理性、具情感性、有行動能力的人類主體,與另一邊無意識、情感也無行動能力的客體。這條界線可以說是現代社會得以建立的根基,在此之上,我們不僅正當化了人對於自然萬物的宰制、剝削,也正當化了其他界線──例如,更理性、更具行動力的男人,與另一端「不足夠」的女人。人與科技物的親密關係、越來越「像人」的人工智慧、越來越「機器化」的人類工作者,這些種種現象質疑了上述鞏固著現代性神話的界線。換言之,如果人不再、或甚至從未獨特,如果那條不可踰越的線實際上是由人自身所建構,那麼我們是否能嘗試打破並重新打造界線,並藉此探索人與非人、男人與女人、或者各種僅僅具有平凡差異的物種的共生之道?
總之,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人的處境。現在,我們全都是賽伯格。賽伯格不是科技浪漫主義中的「超人」(trans-human),但它也不見得如特克憂慮的那般,只會導致人自身以及人與人關係的貶抑。雖然《在一起孤獨》帶著較為悲觀的論調,想要警告我們正輕忽著數位科技發展潛藏的危險。但我相信這並不是最終章,對於特克來說,三部曲也絕非完結。就在去年年底,特克又出版了一本新書《重啟對話》(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顯然地,她試圖延續《在一起孤獨》的討論,並積極地尋找出路。而現在,我們也可以開始閱讀這本書,並思索著自身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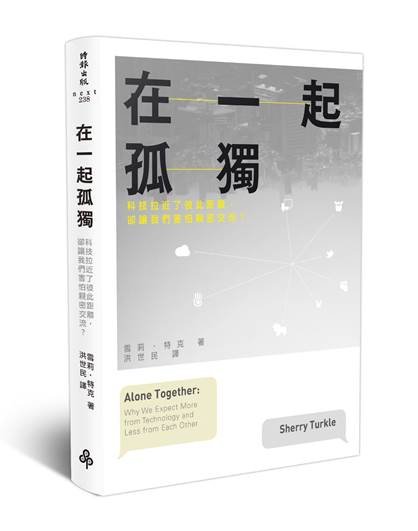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在一起孤獨》一書,本文為推荐序,作者為輔大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本書作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現居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MIT)科技社會研究教授,MIT科技和自我創新計畫(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創辦人兼主任,也是有執照的臨床心理學家。投身科技心理研究超過三十年,被凱文.凱利譽為科技界的佛洛伊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