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通過母親、妻子、女兒三代女人徹底認識一個完整的女人。但女兒們好像並不是通過老爸認識男人。當她們評價男人時,可能把老爸當作同黨,因為太親密,親密得無視父親的性別。
我沒有女兒。
讀《我最親愛的》,寫的是女兒。怎麼最親愛呢?聽說有人寫女兒而成名,或者把女兒寫出名,那必是親而愛,但引不起我的興趣。對此書格外上心,因為是陳浩寫的。也讀過他的《一二三,到臺灣》,兩本書彙集的文章都是寫他和兩個女兒——「父女一場,十分愉快」。我讀了也十分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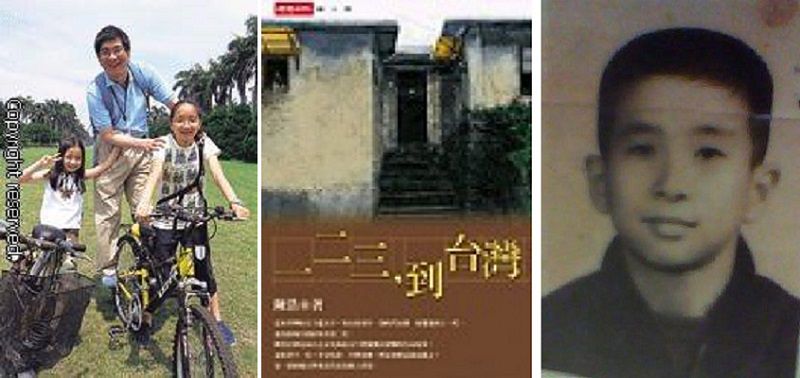
陳浩,臺灣那裡叫他浩子,傅月庵叫他浩哥,我也跟著叫,其實他倆比我小得多。要是拜把子,我老大,但是說為人行事,浩哥真是哥。我們相識,冥冥之中有一種鄉情。他寫道:「長春圍城,父親人在瀋陽,心焦如焚,東北大學師生決定撤往北平,他丟個銅板決定去留,命運讓他向南走,身無分文,作了流亡學生。他在臺灣去世二十多年後之後,有一天老三說,民國七十幾年,父親與老家裡的人通上信,才知道當年爺爺與家人早一步逃出城,到鄉下躲過一劫,長春圍解之後爺爺還與大爺到北平尋過父親,但悽惶流亡的隊伍也已散,父親同學幾十人南下去到了湖南。這都是四十年離亂,生死兩茫茫的上一代的故事,我們弟兄仨聽到的都是片片斷斷,從來也沒湊起來拼圖。」余生也晚,沒趕上長春圍城,上世紀60年代聽老一輩「憶苦思甜」,說那時困卡子,真有賣人肉包子的。圍解之後我父母從哈爾濱南下長春,我就自民國三十八年在長春土生土長,而陳浩的父親再也沒能回故鄉。
看來臺灣畢竟小,我居然結識了好多名家。多數好酒,即便是初見,喝起來也不拘束。有幾位年輕時寫詩,陳浩也「有過自列於寫詩族的蒼白歲月」,給迷戀的女生寫過很多詩,她看了半天,說:「看不懂呀!」也有始終是詩人的,初安民今年春天還曾在舉杯之間給我寫了一首詩。我敬佩臺灣朋友們,例如傅月庵,好讀書,是個讀書家,也常寫書評,正兒八經的書評家,偶爾寫小說,就是小說家,真是想做什麼成什麼,可我總說要寫小說,但寫寫小文章就已經吭哧癟肚。沒讀過浩哥的詩,多少知道他的經歷都是從別處讀來的。我交友就喜歡這種「案發現場」的感覺,頗有點英雄不問出處的意思。他自己寫道:
「我年輕時,追隨司馬文武(江春男)在《八十年代》雜誌擔任過兩年的編輯,後來進中國時報作記者,依舊為‘八十’以及各種黨外雜誌長期供稿。我戲稱同事的田秋堇、劉守成、廖仁義、康文雄等是《八十年代》二期畢業,美麗島事件前的編輯群如林世煜、周渝、林濁水等是如黃埔一期的前輩……
我永遠記得剛進《八十年代》時,江春男就先帶我與劉守成去洗三溫暖,說得有點像入社儀式或河中領洗,反正是男子漢裸裎相見,互信以誠。劉守成與我都很當一回事,我永遠記得當時與守成的一段對話。
『浩子,你為什麼要來八十?』
『大時代的變化就要來,這麼澎湃,我不想置身事外,但我的志向是像司馬一樣當個終身職的記者,我來黨外「參與觀察」。你呢?』
劉守成的答案比我乾脆:『我來參與黨外運動。』
三十多年來,我們都在當初‘『盍各言爾志』的道路上走,劉守成幹到兩任宜蘭縣長,治績有目共睹,我怎麼兜怎麼轉,都在媒體的範圍裡。血管裡流著還是記者Journalist的血,新聞人的魂魄。還是冷眼看著舞臺上的政治人物,成敗腐朽。基本不投票,除非是小女兒拉著我的手,一種公民教育的心情,才去做個樣子。(還很難跟他們解釋我心深處的那把秤)」

在這個小女兒眼中,「老爸就是『幽默、固執、愛讀書、幼稚和肥胖』吧」。固執與幼稚,我不曾領教,因為那種幼稚是「講道理騙小孩啊」。固執麼,好像我甚於浩哥。幾年前他來日本開會,最後空一天,我說去富士山,他說好好好。泡過溫泉用晚餐,我顯出酒鬼本色,執意讓他喝。理由是清酒,淡如水,君子之交也。他可夠隨和,讓喝就喝了。後來知道他患有氣喘,不宜飲酒,簡直把我的腸子都悔青了。聽說他身體欠安時更感到內疚,仿佛那頓酒留下後遺症。
他寫過自己的氣喘:「我的家教是『自食其力』、『不食嗟來之食』,想去橫貫公路,用自己賺來的錢。大二因氣喘休學回家,不敢吃閒飯,以送報生為鍛煉,賺得零用。大學畢業下一個月,就依家規,不再跟家裡要錢。我的家教在今日必被視為農業時代的價值觀,不合互聯網的精神,可我近六年來成立『未來媒體實驗室』,對互聯網時代『分享、創新、連結』的核心價值並不陌生。看『眾募』加『登山』,恕我直言,簡直『胡說八道』,『歪門邪道』,請問這裡頭有個啥互聯網的核心價值?如果強辯稱有,那麼老鼠會也是互聯網不是?有一點點知識真是比沒有知識危險太多了。」
至於肥胖,我與他旗鼓相當。我教他繫和服的帶子,要繫在赫然隆起的肚囊下邊,他說,畫上畫的皇帝就這麼繫腰帶,敢情日本人還是唐朝派頭呢。這大肚皮就不止是小女兒可以趴在上面寫功課、打瞌睡之「另類滿足」了。愛讀書無須多言,他和女兒們談論的日本小說我好些沒讀過,枉在日本三十年,況且還常在出版與文學的河邊走。
浩哥人高馬大,看著就像東北人。我跟他一樣,中學時喜歡打籃球,參加過校隊。我還參加過市業餘體校速滑班呢,但不提當年勇,提了人家若以「體」取人,說出心裡話,那可自找沒趣。反正我的人生已經有幾十年好酒而不好體育了,在十三億體育評論家的時代也從不參與議論。日本友人們喜好,尤其是棒球,談起來哇啦哇啦像鬼子進村,我樂得在一邊喝酒。忽然談到了廣島東洋鯉魚隊比賽,我停杯言道:帶我去看看。他們大惑:熱壞了?喝多了?其實,我一下子想起浩哥大女兒,她喜愛廣島隊,甚至特意學日語,特意去那邊留學。

浩哥常跟我說起,大概以為我久居日本也入鄉隨俗,哪成想我在大陸沒見過棒球,來日本以後也看不上眼。總之是毅然決然,大熱天跟朋友去神宮球場看棒球賽,日本叫「觀戰」。綠的是東京養樂多燕子隊,紅的是廣島東洋鯉魚隊,據說在職棒排行榜上綠隊在前,紅隊在後。這也是我對浩哥父女給他們當粉絲的不可解之處,我所受教育是落後就要挨打。友人知我,沒讓我坐到外野自由席,那裡的助威聲遠遠傳過來還足以震耳。朋友聲援綠隊,我也跟著穿上購票時附送的綠號衣,卻不管輸贏,熱衷看姑娘們背著啤酒桶在觀眾席間上來下去賣啤酒,好似農田裡噴灑農藥。天太熱,像久旱的禾苗喝了一杯又一杯,吃著進場時買好的烤豬排、炸土豆、煮毛豆。綠隊偶然打出了好球,粉絲陣紛紛撐起小傘又搖又唱,倒也挺好玩。看不懂也看出廣島隊打得好,為浩哥大女兒把綠隊打得落花流水,我就把朋友笑話了一通。約定改日再觀戰,友人要挽回養樂多隊給我造成的壞印象,而我覺得在滿場搖旗呐喊中喝啤酒真是再爽不過了。
不過,我記得陳浩是這樣說的:「這廣島像是父女間的密碼似的,一開始她是因為棒球,我是因為讀大江健三郎,就有了共同的花園。她在海綿般吸水的年紀,我卻像個老蚌殼,吞吞吐吐半個多世紀的喟歎,一時一地的滄桑竟牽動兩代人單純的感動,棒球也遇見地球,我愛上的也許不是廣島,而是與女兒青春心田的邂逅停留。」
我貪杯,一杯酒下肚就開始胡說八道,但很少喝斷片兒,因為到底沒那種何妨醉後死便埋的豪氣。好多年前朋友們邀我去臺北參加國際書展,那時陳浩剛從電視臺轉職搞什麼高端的傳媒玩意兒,他的老闆設酒宴,不知怎麼一來,我就和王健壯拼起了金門高粱酒,一杯一杯複一杯,終於斷片兒了。翌日,努力恬然著昨夜的醜態,和浩哥一撥人去喝茶,路上遇見他女兒。小姑娘先衝著大家靦腆一笑,再轉向老爸,眼神就有點咄咄:你又去哪兒!偉岸的父親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父親看著女兒長大,女大十八變,但女兒們好像並不是通過老爸認識男人。當她們評價男人時,可能把老爸當作同黨,因為太親密,親密得無視父親的性別。男人通過母親、妻子、女兒三代女人徹底認識一個完整的女人。浩哥跟女兒們討論「娘」,最「娘」的不就是老爸麼?小女兒說:「在家撒嬌、耍任性的也好像都是他這個做爸爸的!」女人是水,女兒是最純的水,把濁男子滌蕩得一片純真。說是寫女兒,其實也在寫女兒眼裡的自己。有女兒們襯著,字裡行間的浩哥更可愛,真想灌他酒。但是說實話,他的書我唯讀了一遍,而兩位寶貝女兒給他寫的序我讀了好多遍還想讀。
給女兒當老爸真好。

*作者為旅日作家。(原文刊登騰訊大家網,原題:〈我這酒鬼和浩哥以及他的女兒們〉,取得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