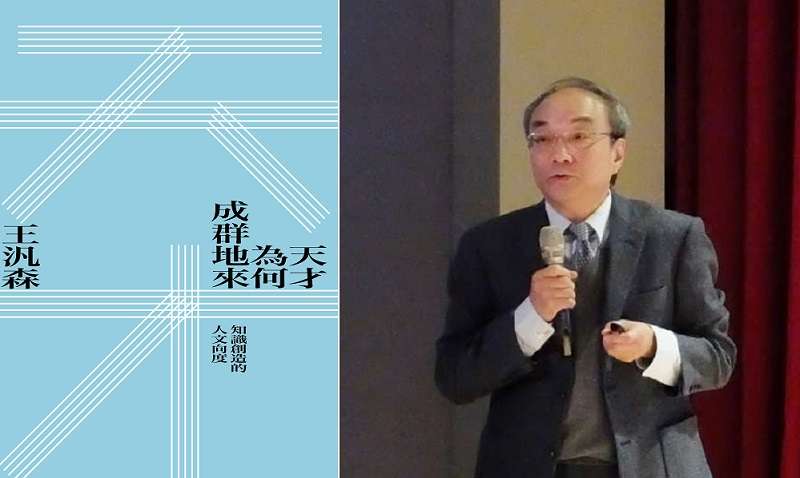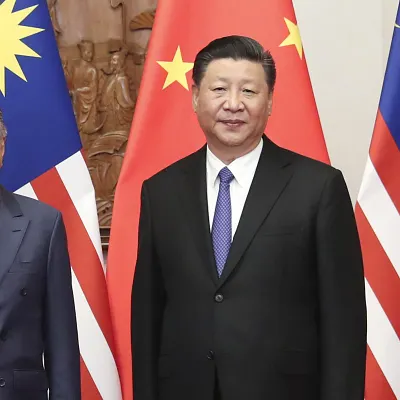十六、七年前,當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時,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報刊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我便開始零星地蒐集這方面的文字,並準備寫一篇長文(甚至是一本小書)來加以討論。而且我的討論將盡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學術論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不必再經過我的重述—可惜因為個人疏懶,這個願望遲遲未能實現。最近承《數理與人文》出題讓我寫一篇「余英時印象」,因為時間比較倉促,我只先選擇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筆。
我是在一九八○年,《中國時報》在宜蘭棲蘭山莊舉辦的一個閉門討論會上初識余先生的。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所有參與者,後來幾乎全部成為中研院院士或是內閣部會首長。我記得當時偶然有機會向余先生請教我的碩士論文《章太炎的思想》,曾提到當時大陸正在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動作太慢,深怕資料不足。余先生說史料不必勉強求全,但論旨要集中(原話是要有 focus)。還記得當時余先生棋興大發,與胡佛先生等人對弈,在座者都不是他的對手。由於我在一旁觀戰,余先生還轉過頭來問我:「你下圍棋嗎?」後來我才知道余先生業餘六段,得過新英格蘭地區本因坊,甚至還參加過在紐約的世界圍棋大賽。據我觀察,余先生似乎在學習與上手之間,時間距離特別短,學詩、學戲、學棋、學書都是如此。這當然也讓我想起一九八○年代後期,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余先生有一度前往紐約與林海峰對弈的往事。
一九八五年,我從士官學校退伍,準備申請中研院工作。當時思想史在台灣學術界如日中天,史語所願意招攬思想史方面的新人,而我也極其幸運地以碩士身分進入這個傅斯年口中的「天下第一所」擔任助理研究員。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的審查者之一,竟是余先生。
我真正有機會近身接觸、觀察余先生是在一九八七年到普林斯頓讀書之後。可惜在普大的五年中,因為課程太緊張,學期報告太多,每天「夾著尾巴」央求人改英文,居然沒有記日記,連僅有的三冊上課筆記也淪陷在我的書海中,一時無從翻撿。現在回憶舊事,腦袋一片空白,翻來覆去就是那幾件事。胡適說得好,人的記憶倏乎而逝,如果沒有一片紙記下來,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胡適記了幾十年的日記,留下了一部寶貴的史料)。無論如何在那五年半間,我注意到余先生治學的幾個側面。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首先,余先生是隨時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細審度每一個問題,而且異常的專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讀書,似乎字字是立體的,讀一句有一句之用,讀一段有一段之用,它們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物連類」的功夫特別強。多年前中研院有一位同事寫了一篇與錢謙益有關的研究,余先生匆匆一閱,便馬上說它與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的一個片段相出入。我個人對《柳如是別傳》並不陌生,但因為《柳如是別傳》的敘述濃厚、每每還有一點枝蔓,所以完全沒有把兩者想在一起,這是一例。去年我偶然從史語所的「杭立武檔案」中見到一九四九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長杭立武報告的信。信中報告說黃霖生已經到廣州勸陳寅恪一家來台。寫信的章丙炎說黃霖生已經見過陳寅恪,但陳寅恪「因在鐵幕內受片面宣傳影響,對赴台深躊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這封信,余先生馬上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與這封信比觀。去年我受人之託,傳真了一篇《祖國周刊》的文章(凌空,〈介紹反共文化運動中的兩個學派〉),請余先生確認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筆。不意余先生很快地就回了一封傳真,推測作者應該是某某人,而這位先生曾經訪問哈佛,做過楊聯陞先生座上客,後來未再見過等,把握精確,絕不含糊。
余先生的工作習慣是徹夜不寐的,所以我剛到普大時有幾次早上十點上課,覺得他臉色灰黃,有點站立不住的感覺。我也曾針對這一點請教余先生,他的答覆是:人是身體的主人,身體聽我們指揮。意思是這不算什麼。而余先生當時煙癮正大,在普林斯頓大學時便聽說過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菸,駕車到普大附近的 WaWa 買菸的故事。此外,我記憶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長夜之談。余先生熬夜長談的本領真高,在節日前後,他每每邀請學生與訪問學者到家裡吃飯,並做長夜之談。這類長談往往持續到凌晨三、四點,當坐客皆已東倒西歪之際,余先生仍然從容地吸著煙斗或紙煙。
在我中學生的時代,台灣正流行一種做卡片的運動。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當時的名稱是「中央卡系」,我也曾受這波宣傳的影響,以為「卡系」是一點就通的治學利器。而且一般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為了輔助記憶力之不足,往往也比較系統地做卡片。我就認得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家,如果忘了帶他的制式卡片,是不進善本書庫讀書的。因此,我曾好奇地問過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說,除了早年為《後漢書》做過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記筆記,不做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觀察沒錯,余先生讀書也不太劃線,與毛澤東「不動筆墨不看書」至為不同。甚至上討論課時,也不大抽筆記學生報告的重點。好似他的腦袋中有那麼幾個匣子,有意義的材料會自動存在裡面,等他開口評論時,只要依次打開那幾個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期間,我曾一度回母校,為了旅途解悶,余先生曾將一、兩章稿子交我閱讀。這時我注意到文稿中夾了幾張廢紙,上面零星地記著幾個詞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寫時所依靠的線索。至於余先生撰寫短文時,似乎是沈心研玩某些書之後,在腦海中形成幾條主要線索,然後將書閤起來,繞著那三、四條線索,一氣寫成。在寫作的過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時才會回去翻檢原書。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陳確(乾初),他說自己詳思多少年之後,決定判《大學》為偽經,乃下筆「快寫一過」。或是像陽明在頓悟良知之後,憑著對經書的記憶,快寫而成《五經臆說》。至少這是我讀余先生的〈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覺。
余先生撰寫研究論文時,顯示一種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達方法,也就是說他並不像清代考據學者動輒擺出「證佐千百條」,他只擺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證時,往往是一、兩條,或兩、三條,其他證據則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學術論文讀起來一氣呵成,沒有冗贅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近來由於電子文獻資料庫的發達,往往一按鍵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捨,容易出現過度水腫的情形,失去了閱讀時的暢快感。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余先生閱讀的方面非常廣,如蜜蜂採花釀蜜,但大多備而不用。等到要寫某一篇文章時,各種資源自然群到筆下,這也還是「冰山一角」式的作法。依我學生時代的觀察,他對當代正在發展的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這中間包括像 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urgen Harbermas、Paul Ricoeur 等人的書。那些年代余先生飛行機會比較多,坐飛機正是他讀書的時候,我記得 Richard Roty 的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一書就是他在從台北飛到紐約時讀完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手上還留著一張紙條,是余先生託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總館幫他借《重訪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Revisited)。
余先生極少託我們這些研究生做事,他是所謂的「單幹戶」。從作研究到寫文章,全部一手包辦,純粹農業時代的手工作風,頂多請系祕書幫忙繕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謹慎的。最近我有機會讀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滿紙鬼畫符。
余先生是不碰電腦的。記得他在二○○六年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時,我正好遇到翁啟惠院長,提醒他因為余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所以應該送一封賀函。過了幾天,再度遇到翁院長,我問他送了嗎?他說送了。我問用什麼方式,他說電郵。我急呼:「余先生沒有電腦,也不收電郵,您的郵件送到哪裡去了?」至今,這還是個謎。
余先生一九五五年離開香港到哈佛,他是帶了許多當時華人學界的關懷與困惑前往的,故他到哈佛之後便關心希臘時代、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等主題。此外,關心余先生早年寫作的人,已經注意到余先生在香港時期的少作,都肯定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而且文章最常出現的詞彙是「思想」、「文明」。但在香港時,他的研究是以社會史為主,即使在美國擔任教職初期,仍是以廣義的社會經濟史為主,後來才逐漸轉向思想史。所以我推測余先生早期有一個思想與學術複調平行的發展,後來逐漸歸於思想、文化一路。
在二○○七年一篇題為“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 (Diao (2007) 6:39-51)的文章,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余先生身處的時代學術環境中馬克思主義歷史命定主義影響甚大,認為文化、意識是被社會經濟所決定,歷史是被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後的發展似乎對這類帶有決定論色彩,或認為歷史有通則的思想進行徹底的反思,強調文化及意義的自主性,同時也強調傳統。他說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讀柯靈烏(R. G. Collingwood)的《歷史的觀念》時,深為其中許多討論歷史知識的特質、開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個事件的內在與外在部份,像歷史知識是一種對過去思想的追體驗,當時覺得比起那時最為當令的 Carl G. Hempel 的歷史通則(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說服力。
余先生在文化上有許多主張,值得深入探討。在這裡,我只想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余先生從年青時代起,對自由、民主的理論便做了很多討論。如果我的了解不錯,在一九五○年代,由於國共政權之更迭,使得究竟是走西方自由之路,或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強調分配上的平等,是相當熱門的問題。傅斯年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如果只有自由而沒有平等,那樣的國家他不願意住。如果只有平等而沒有自由,那樣的國家他也不願意住。他心中比較認可的,是像羅斯福「新政」時期那樣兼顧兩者的政治。如果我的了解沒錯,余先生《自由與平等之間》等論述,便與當時思想界渴望得到解答的想法有關。除了自由與民主的討論之外,我覺得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提到的「背景文化」是值得注意的。簡單的說,在民主與自由的時代仍需要有一個「背景文化」,否則它們是行不通的。我覺得余先生從早年在討論自由、民主的時候,便與這個「背景文化」的觀點暗合,所以他在那個時期的許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國傳統文化。當時他曾經給《自由中國》投過一篇文章,認為提倡自由、民主仍不廢儒家文化。但是,這篇文章被拒絕了。因為當時台灣知識界的主流派認為,若想推行自由、民主就要以清除傳統文化的阻礙為前提。一直到近年,我覺得余先生更加自覺「背景文化」的重要。他在「余紀忠先生講座」以及唐獎漢學獎的座談中,都強調「人文與民主」,也就是認為豐厚的人文素養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背景文化」。
最近我才驚覺當年負笈普大,在系辦的走廊巧遇余先生時,余先生正好就是我現在的年齡。那時余先生精神颯爽,名滿天下,剛從耶魯大學的講座教授轉任普林斯頓大學的全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沒想到歲月不居,轉眼過了將近三十年了,時光飛逝,不免令人深深感嘆。
(相關報導:
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天才為何成群地來》(允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