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閉,
所有的眼淚都被監控,
所有的鮮花都被跟蹤,
所有的記憶都被清洗,
所有的墓碑仍是空白。
劉曉波,〈六四,一座墳墓〉(二〇〇二年)
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二〇一七年在獄中死於癌症。二〇〇二年時他寫下這些詩句,稱六四為「一座墳墓╱一座被遺忘所荒涼的墳墓」。對曾於一九八九年勸天安門學生做最後撤離的劉曉波來說,六四始終是他身體裡的一根針,「它常常游弋到心臟的邊緣……偶爾會用針尖試探地觸碰心的表面。」這二十年來,他每年都為六四寫下紀念輓歌,像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懺悔。極其悲傷諷刺的是,如今他筆下那些被禁止的記憶,不僅僅只是在寫一九八九年逝去的冤魂,也是在寫他自己。劉曉波的遺體是如此強而有力的象徵,中共為了避免他的墓地成為朝聖地,倉促主導了喪禮的安排,並將他的骨灰撒入海中。
三十年過去了,天安門事件的記憶沒有消散,反而變得益發敏感。

長年以來,公開的紀念活動都被禁止,近來當局甚至開始越來越常懲罰私人的紀念活動。二〇一四年,十五名知識分子在一處私人住宅內舉辦二十五周年紀念聚會,後來其中五人被捕,並在幾天內被冠上「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國家不僅監管集體的記憶,更是積極將監控的觸角伸向個人。為了避免禁忌思想溜進公共空間,提醒其他人必須遺忘的事,中國當局連人民的腦袋,這樣私密的個人空間也不放過。
中國共產黨對六四事件有多麼恐懼,從它近年如何把記憶當作一種罪來懲罰就可見一斑。二〇一七年,四川異議分子陳雲飛被判四年有期徒刑。他的罪行,只是為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死去、葬在成都郊區的學生吳國鋒掃墓。隨後,陳雲飛就被控以「尋釁滋事罪」。從此可看出,這個國家多麼嚴密地管控它的人民,連人民私底下到郊區掃墓,低調到沒人會注意到的行為,也會覺得應該施以懲罰。正如小說作家鄧敏靈(Madeleine Thien)所言:「可以說,沒有人比中國政府更忠實、更專注地記得天安門事件。」
還有另一宗歐威爾所謂的「思想罪」(thoughtcrime)發生在二〇一六年,四名男子精心設計了一瓶紀念款白酒,酒標圖案的靈感來自那張在長安街上與一列坦克車對峙的「坦克人」圖像。這四人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四川成都對一九八九年血腥鎮壓的集體記憶,早已被抹滅殆盡,上述兩起案件卻都發生在成都,這並非巧合。今日的中國,歷史是由當權者決定的。法律規定,任何歪曲或貶損歷史英雄及烈士的行為都是刑事犯罪。

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清洗與重製的工作上成效卓越,尤其是關於成都發生的事件,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幾乎無人聞問。套句牛津學者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的說法,「主動的逃避者」(active complicity,即一九八九年已懂事卻宣稱自己不知的人)與「被動的無知者」(passive ignorance,即一九八九年以後出生且一無所知的人)通常只有一線之隔。儘管中共可說是大獲全勝,但它顯然依舊戒慎恐懼,對任何再小的公共紀念行為都風聲鶴唳,深怕有人玷汙了純淨的集體記憶。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特意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我從不在家裡或北京的辦公室提及這本書。我也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這本書。我隱瞞了我的孩子好長一段時間,只跟一小撮人透露我在做什麼。我不使用連上網路的筆電寫作,並且都把稿子鎖在臥室的保險箱裡。離開中國之後,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不再習慣性地壓低著聲音談論六四。我意識到,在中國住了十年之後,我也把六四禁忌內化了,要打破那種沉默桎梏常讓我想吐。
我還沒意識到的是,藉由書寫這本書,那些被禁止的記憶終會被解開,或被釋放。我後來在美國、英國、香港、德國和澳洲的大學的幾十次演講中,一次又一次地目睹這個過程在我眼前展開。我在演講中展示了一九八九年的官方資料,例如中國當地的報紙、宣傳單、內部的報告,也分享了見證者的照片和日記。對一些在場的聽眾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看見這些東西,曾經一無所知的事件不再是未知。
我第一次演講是在二〇一四年。一位中年的中國婦女站起來問了一個問題,她想知道當時的學生運動是否有受到海外的援助。她接著問了第二個問題,口氣宛如在請求寬恕:「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的一切都是真的嗎?」她問,「有任何一件事是真的嗎?」她削瘦的身子明顯在發抖,冷靜的提問聲夾帶著一絲顫音。許多年以前她選擇了主動逃避真相,那個過去的她就在剛剛被衝擊改變了。

還有一次我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演講。我注意到台下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一動也不動地坐著,聚精會神地聆聽。當我講完後,她當著一屋子的美國同學站起來說了一段話,「我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對我國家的歷史一點兒都不了解,」她說,「我上的是最優秀的學校,管理最好的學校。而我對一切都一無所知。」就在此刻,她的無知時代已經結束了。
對一些目擊者來說,遺忘則是一種必要的自我保護機制,可以抵禦那些巨大到無法言說,且尚未解決的創傷衝擊。我在成都遇過一群人,他們學生時代時曾上街抗議,親眼目睹了鎮壓過程,卻對後續發生的事撇過頭去,不再思考。某一次在歐洲一所大學的演講裡,一位優雅的中國女士講述了自己在此之前,幾乎遺忘了她也曾經是成都抗議遊行的一員,甚至在當地一家醫院親眼目睹政府暴行下的受害者。「儘管我來自成都,儘管我人就曾在當地,因為天安門對成都人的記憶來說太重要了,但我對成都的記憶某程度上已消褪於陰影中。」她說。對其他人來說,這個創傷讓他們失去了原有的純真,他們的希望殞落,夢想幻滅。
周年紀念可以讓社會有機會認真地反思,並大聲地把想法說出來,努力解決過去歷史事件遺留的問題。但是當公共事件的記憶被壓抑時,社會就無法追究相關責任、反省檢討,以及讓為惡的人付出代價。對今日一些年輕世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保護自己,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他們深信,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的,任何偏離這一基準的行為都是魯莽的,甚至是危險的。二〇一八年六月,在澳洲一所大學擁擠的教室裡,一名年輕女子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觀點。她並非用質疑的口氣,而是發自內心好奇地問道:「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段歷史呢?為什麼你認為了解這段歷史對當今、現下的中國,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有幫助呢?你認為這樣做可能會威脅到中國所謂的『和諧社會』嗎?」後來,另一名中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是否思考過,僅僅是關於六四的知識也可能對「我們完美的社會」構成危險。

對我來說,這還不是最難回答的問題。有一些年輕的中國人會在演講結束後,在四下無人的時候偷偷地來找我說話。他們躡手躡腳地走到桌子邊,以我幾乎聽不見的聲音,用不同言語問同一個問題。這個問句隱含著一種無聲的指責,像是控訴我戳穿了他們的無知。他們想知道的是,到底他們應當拿這些新知識怎麼辦?既然他們知曉了真相,接下來該做什麼?我都這麼告訴他們,去吧,盡你所能地去挖掘真相吧。盡其所能地閱讀所有能找到的各種資料。利用你手中一切的自由來獲取知識。你應該自己決定要接受哪一個版本的國家歷史。如果你願意,與他人分享你所知道的六四。更重要的是,要銘記不忘。
未來的路通向何方,台灣對二二八屠殺這段歷史的處理上或許可以作為某種示範。也許有一天,天安門廣場會建起一座紀念博物館,就像台北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也許有一天,中國也會有個一年一度的國家紀念日,就像台灣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然而台灣面對二二八大屠殺的這段平反之路也走了四十八年,中間還歷經了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之後又過了十六年,才有了現在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此同時,讓那些記憶保持鮮活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當捍衛自己的歷史記憶,並抵禦來自北京近來頻頻試圖跨越國界,干擾控制他國輿論的侵犯行為。落筆至此,我想起劉曉波在六四十五周年寫的輓歌的最後一句,以此作結是再適合不過了:
在絕望中,
唯一給予我希望的,
就是記住亡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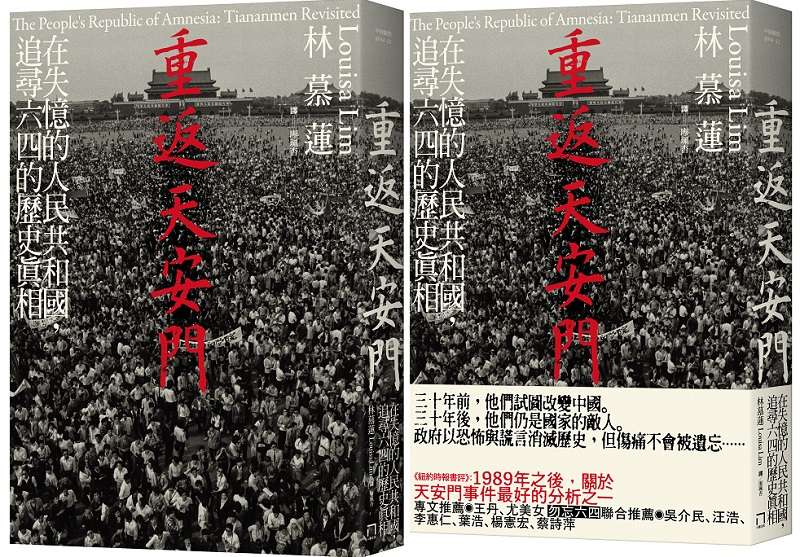
*作者林慕蓮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本文選自作者在天安門事件25過年應牛津出版社之邀所寫的《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八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