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夜晚散步時,總會聽見小號吹奏的聲音,從斜坡旁藏匿在樹叢後,燦亮的管樂社辦流瀉出來。那小號的聲音帶著斷續的生嫩,時而若分岔的羽毛傾斜幾個音符,彷彿看見一隻翅翼未乾的雛鳥,歪斜地展開小小的翅膀練習飛翔。
不知道為什麼,在那樣的漆黑之中,聽見這樣的吹奏聲卻讓人有種置身透亮清晨的錯覺,興許是旋律之故,興許是那不純熟仍帶著生澀的音樂,都讓人感覺置身在那種將明未明、好似可以一直漫無目的地拖曳步伐,淡漠如畫的清晨。
我已經許久未曾擁有那樣的清晨,一如已然遠離那段輕盈而伴有樂器的日子。在那樣的時光裡頭,潛入一個沒有光的地下室,祕密聚會般的,和一個擁有曼妙身材,留著一頭大卷長髮的美麗老師學習長笛。那些僅擁有旋律的日子讓人感到懷念,彷彿日子被梳整為純然的五線譜,只須在那之間跳動。

這樣的時光約莫維持兩三年便被升學壓力給吞噬。往後我便把擁有的兩支長笛(一支是初階的閉孔長笛、一支則是開孔)收納在如若叢林般的衣櫃裡,偶爾會想起銀亮的它們如蛇般棲身在幽暗的盒子裡而感到滿心愧歉。
銀亮之蛇在夜半摩娑鱗片,對著回憶嘶嘶吐信,那分岔而細弱的舌上讀到了怎樣的氣息?
有時會想起,當時的母親為何讓我學習樂器以及其他才藝?無非是對於養育一個女兒充滿浪漫幻夢吧?然而家中其實並非什麼藝術之家,母親大概是受到身邊朋友的影響,加上自我對於養兒育女的拼湊圖像。每次思緒至此,心口總會一陣緊縮。
那或許是突然想起,曾有那麼樣的一個人以樸拙的姿態,對於描繪你未來的輪廓如此熱切,內心盈滿希望。而我對於這種「懷有盼望」的心理狀態,經常感到難以形述,像是不經意地用指尖碰觸了一條擺放平穩的棉線,陡然在心中岔出一種不忍的心緒。這種不忍的怪異情緒或許包含了,不忍看那被懷有盼望而描繪出的自己,不忍回應那樣的懷有盼望。也或許是那原先就蟄伏在體內的悲觀,總是對於人類充滿盼望的這種狀態感到一絲不安,害怕那些盼望最終都散佚在空中。
畢竟世事總是生住異滅。
如那些鬆開手便向上飄升的氣球,最後因大氣壓力變化而終究爆破開來。(兒時的我總花費很多心思在想像那些氣球最終的模樣,它們在哪爆破開來的?是否曾經有人恰好遇見飄落而下的氣球碎片?而誤認它們是花瓣?)
對於那種過於晶瑩透亮,全然信任著某樣什麼的澄澈神情,總不經心的感到一絲憂慮,也或許這全然是沒有必要的。因為世間確實是有什麼?有什麼是值得相信的吧?即便這個承接信任的載體如何地渺小,如何地被他人所忽視。
但也總該這樣相信?若在生活裡懸著一條線,便總有什麼能夠昂然面風的掛上?
認識那個也學長笛的妹妹五年了,五年,十年的一半,聽起來就有些恍惚。五年前剛成為妹妹的家教老師時,小學五年級的她臉龐上盡是純真,卻能夠看見她因為家庭環境有所餘裕,而比同齡學生得以接收更多教育資源,因而從眼神之間淡淡流出的一股傲氣。那傲氣雖然淡淡的,卻散出涼氣,似乎逼視著你:你有什麼?
家長待我極好,只說想讓妹妹學寫東西,讀文學作品,對成績漲幅無所要求,放任得幾乎不像世事。每次從影印店印出講義與文章,紙張的熱氣傳遞到指尖,像一種尚有體溫的活物,令人感到不安。雖然自認每一次都選了內容豐厚的文章。但還是難以避免在上課前的路途中想及:我真有辦法教予她什麼?
究竟要給出多少真心?(那有點像是究竟要把《小王子》講成一個可愛故事,還是講成哲學故事的問題。)在任何一篇文章裡,多講擔心她感到無趣,少講又感到一絲可惜。而少話的妹妹總是微笑地看著我點頭,問她所有問題她都僅是點頭抑或搖頭,投來一個恬靜的微笑,偶爾吐出幾個短句子搭話。

有時出幾個搭配文章的小習題,她低頭書寫時,我便空然地轉動眼球(切不可太大幅度轉動脖子使人感到家中被窺視)觀察我們所在的空間,這是廚房裡的一張大桌子,左側掛有她很是成熟的圖畫作品,右側有能透進陽光的大片玻璃,廚房相當整潔,內側蹲伏著Tiffiny綠的大同電鍋,桌子的邊緣擺著各式進口零食、沖泡包。(噢,每次上課我總有零食和飲品得以享用。)
最終視線落在那幅筆觸細膩的圖畫上,畫的是西方街道,妹妹說她喜歡西方國家、喜歡城市和冷氣,一切舒服整齊明亮的事物。想起幼時的我也學畫,也和她學了同一種樂器,她得知後露出一個很大的微笑,彷彿我跟她之間多了更緊密的連結。但心裡卻深深明白我們之間的不同,那種奇異而曲折的感覺是:我是虛的,但你是實的。
我一定比她更明白,她那溫柔又身為高知識分子的母親是多麼有意識地想將她培育成一位才女,除了寫東西和繪畫,她還學了芭蕾、現代舞、鋼琴。有天去上課時,她家寬敞的客廳忽地就出現一架豎琴,妹妹說那是她最近新學的樂器。豎琴,那種狀若羽翼的夢幻樂器,彷彿倚著它彈久了便擁有飛翔的資格。不對,它落降在客廳本身就是一種資格。
因此有陣子上課,總幻覺這位妹妹身上纏繞著許多許多晶瑩發亮的事物,我想起關於期待這件事,她必定也被給予了許多期待與祝福,思緒及此,胸口便又緊縮起來。過於美好的人,過於美好的事物,譬若繁花開盛,盈滿氣體的渾圓氣球,那隨時便要飛至藍天的神情。
總會不住的想及,如此幸福之人/嚮往舒服整潔之人,真能理解某些文章裡出現的不幸之人/灰色汙漬嗎?或是,她真的有必要知曉這些?(如若能夠毫無負擔的生活著,不也很好?)(或許也只是我自以為是的想法)但即便心裡總帶著這些疑慮,實際上也不甘心只剝開一些溫婉的成語字詞,不甘心僅是剝開一層皮。
但究竟要剝開的是什麼?剝開後又有什麼?那是否僅是一個虛晃的手勢?只因我們都對於世界內核的祕密心照不宣:那裡頭其實是空心的啊。
我參與了這個妹妹被賦予期待的過程,在她身上那一串晶瑩光亮的投注裡,總感覺自己是一截多餘的梗,被錯誤地扦插在一片花園。因為我太懂得他人的分析。輕盈甜美柔善,如若許多人對於文學單方面的誤會,以為那必定是風花般蕩漾的事物。
妹妹低著頭沙沙寫字,我看著她換過一個又一個不同顏色的筆袋,寫錯字時迅速抹上立可帶旋即丟捨,如若廚師麻利切肉的模樣,那使人嗅到青春的息氣:錯誤的,切掉就好。
五年,那手持長刀將十年剖半的年歲,露出鮮紅多肉的內裡。不知道這位妹妹為何堅持上課。每一次相見的時光皆像玻璃桌下壓的扁平而乾燥的花瓣(因如此自由的上課模式抽空了現實感)。我總是獨自說了許多的話,那些話在這麼多個安靜的午後該是流沙般沉積到她的心內,而我並無法知曉,聲音與字詞在我與她身軀的傳遞之間產生了怎樣的變化?
我究竟在她身上默默淤積起一座怎樣的小島?開出什麼樣的花?
結束課程的時間經常落在傍晚,推門走出時常是一片將要墜入夜裡的深灰藍,走在周身皆是樹的斜坡道上,總懷疑起這路途的真實?腳步的真實?那如此美好的少女與房子是否僅是一幢蜃樓,有一日我將忽地再也找不著這對美好的母女。
時光錯落交織。
想起和另個小男孩在課堂上的對話,小學一年級白淨的他突然仰頭說道:
「老師,有時候我會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我會忘記自己是誰。」
「晚上有時候很黑,我做夢時,不知道自己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摸一摸他的頭,微笑。心裡想著沒關係的,我到現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自己是誰,自己是真的還是假的。我想有一天可以和他說說莊周夢蝶的故事。
一年級的小弟讓我想起《雷峰塔》裡的一段話,記得初讀完《雷峰塔》時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張愛玲最想寫的其實就是這段了:
琵琶嗤笑著,自己也知道無聊。碰到這種時候她總納罕能不能不是她自己,而是別人,像她在公園看見的黃頭髮小女孩,只是做了個夢,夢見自己是天津的一個中國女孩。她的日子過得真像一場做了太久的夢,可是她也注意到年月也會一眨眼就過去。有些日子真有時間都壓縮在一塊的感覺,有時早幾年的光陰只是夢的一小段,一翻身也就忘了。
因為碩論的關係,必須長時間與張愛玲(晚期的)廝混在一塊兒,有時恍惚感覺身在她筆下一間又一間幽暗飄散著鴉片煙的房子,陽光非常老舊,彷彿遺忘所有,四周嘈雜轟亂的人聲,腳步聲細細碎碎,時間悠緩得如同她筆下反覆描寫的映著日光,金蛇一般的麥芽糖。《雷峰塔》中的琵琶總心急地等待麥芽糖緩慢的流下,而那麥芽糖就是時光,時光如此緩慢,卻又一下就長大,而長大後卻又必須直視所有殘忍的物換星移。
一年級小弟的課本上寫:
蝴蝶姐姐請問你:
「花開怎麼沒聲音?」
蝴蝶姐姐笑一笑:
「花開的聲音小小小,
只有我和蜜蜂聽得到。」
是啊,我們都聽不見花開的聲音,聽不見時間和夢,我們如何在人與人之間物換星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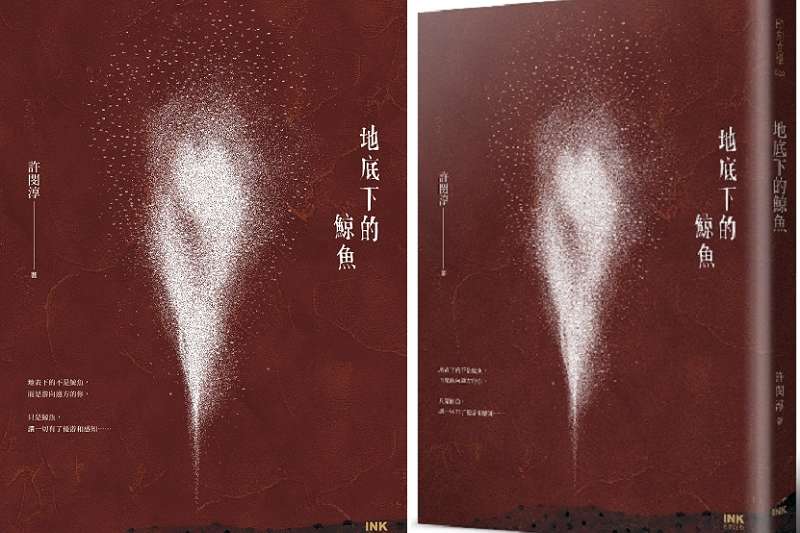
*作者許閔淳為90後年輕作家,曾獲多項文學獎。本文原自作者散文結集《地底下的鯨魚》(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