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我應該不算「文季」的同人,雖然我也參加了發刊在明星的聚會,面對一堆人,我還是不自在。跟朋友談聊我會輕鬆言笑,可是遇到不熟的一群人,常不知如何措放手足,這也是我很少參加文學活動的原因。
雷驤,七等生,簡滄榕和我常聚在一起作深闢的談論,雖然很多是個人臆度而加以誇張擴散,卻是非常精彩,有些場景到現在還是很懷念,繪畫,音樂,電影,文學便在互相啟發而樹立了自己的格調。當時二十多歲,真正寫得比較勤的是七等生,遭遇的挫折也比較重,而我跟大家談說完理念情節,好像作品就完成了,所以留下很多殘稿。我比較專注認真寫作是在民國七十幾年,父母相繼過世,與生命存活的關係突然緊張起來,文字表涵便成為我和它交通連繫的工具。
除去臉書部落格等電子傳播,單就報紙雜誌,現在要發表小說反而比三四十年前困難,園地越來越小,那能容得下那麼多的俊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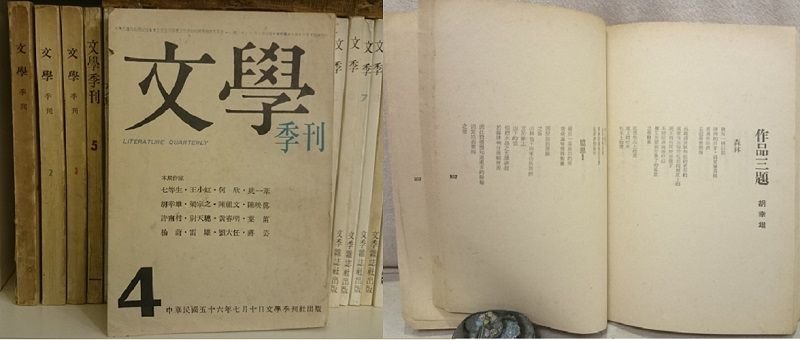
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老師算得上是非常活躍的小說家,一九八七年圓神版《浮生》,一九九一年三民版《黃昏過客》讓人印象深刻,許多朋友至今聚會還時常聊到這兩本很特別的小說。
關於小人物的命運及其窘迫的人生,您常有獨特的觀察視角與筆觸。從《浮生》到《黃昏過客》,我們也可發現老師在敘事技巧力求突破,用字遣詞力求精準的努力。是否談談這兩本小說的創作意圖,或說其所想要表達的東西?
沙:其實我並不太喜歡談說自己已經完成的作品,寫詩很暢快,寫小說很辛苦,完成後像擺脫一件糾纏不清的事情,不太想再去復習,寫完就算了,其他的就由別人去談論。
「樸素心靈」一直是我所關懷的,有些人能夠對別人真誠,善意,吞忍,遇事默默承擔,這就是我說的「樸素」。在他們生活範疇裡,究竟展現怎樣的輪廓?我的興趣在此。有人或許會說:素樸不能成為眾人的道德典範,我卻認為它是最珍貴的,最為貼近「為人」的原型。母親對我們兄弟作情緒性的打罵雖是難免,終其一生我沒有看過她和別人吵過架;士林過港有位親戚,平日受盡媳婦惡待,鄰裡都知道,在媳婦難產時,燒香祈天歸責於己,把剛煮的一鍋飯倒進廁所以示惡行。這些都是我有興趣去深思的,多少是我寫作的一些動力。
此外,我對超現實主義也有興趣,這一主義與其說是繪畫,毋寧說是文學。有所構思,盤旋腦際盡是這樣的畫面,我就習慣以此去表敘我的文字景觀,那種沁人內裡的融合是極度暢情的。
傅:在停筆這多年之後,您似乎重染寫小說的樂趣,其中有何因緣嗎?此時寫作的心情與昔日有何不同呢?
沙:我並沒有徹底停筆,斷斷續續我寫了許多筆記和未經修改的小說,作為宣洩情懷的出口。兩年多前,我回士林探望兄弟,街口繞了一圈,坐在慈諴宮廟門前石階小憩,看到前方戲台前塞滿了俗不可耐的石雕,想起念小學的年代,尚未建戲台,兩棵高大的榕樹分佈左右,整座廟宇是在和諧的空間裡散佈它的靈氣。現在消失的不僅是童年的眼睛,連空氣中也瀰漫一股午後的呆滯之氣。
回桃園以後,想去批判廟宇執事的心安靜下來,我很平順地寫了〈群蟻飛舞〉這篇小說。寫小說當作自我生命的擴張,從理路張羅視眼見不到的綺秀,以此融入真實,長久鈍化了的這種感受彷彿又回來了,我陸陸續續整理許多殘稿,這工作將持續進行。
(部分節錄)

小檔案:
沙究
本名胡幸雄。一九四一年生,臺北士林人。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長期擔任中學教師,現已退休。作品曾獲中國時報短篇小說推薦獎、洪醒夫小說獎。著有短篇小說集《浮生》、《黃昏過客》。
傅月庵
本名林皎巨集,文字工作者,文章散見兩岸三地報紙期刊。曾任出版社總編輯、二手書店執行總監,現任「掃葉工房」編輯工作室負責人。著有《生涯一蠹魚》、《蠹魚頭舊書店地圖》、《天上大風》、《我書》等。即將出版新作《一心唯爾》。
(完整內容刊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2015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