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梁濟的敬告世人和譚嗣同的慷慨就義,王國維的自沉方式呈現出更為純粹的非功利的審美氣度。這樣的氣度印證了他在文學藝術上的非功利的「遊戲說」,即「文學、美術不過成人精神的遊戲」,而這種遊戲的根本意味也就在於其純粹的審美。基於這樣的審美立場,王國維的自沉連同其艱難困苦的人生旅程不是事功的、濟世的,也不是體現獨善其身之生存策略的,而是藝術的、審美的、體驗的。如果說悲劇意味著一種巨大的審美快感的話,那麼王國維的自沉則正好是這種快感的全身心的體驗。由於如此深入的生命體驗,王國維走向昆明湖的腳步並不像人們通常想像的那麼沉重那麼淒慘,而具有一般人所無法想像的平靜和愉快。因為這腳步即沒有「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式的迷惘,也沒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焦灼,從而全然洋溢著「夢裡尋他千百度,回首驀見,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欣喜和恬然。相形之下,梁濟死得迷惘,譚嗣同死得焦灼,唯有王國維死得寧靜,宛如一味淡淡的清香,在投水的一刹那從昆明湖上飄散開去,縈迴於天地之間,觀照出人世的苦難,觀照出歷史的劫變。遺憾的只是,當時的呼吸領會者,獨寅恪而已。
從上述三種不同的赴死境界上,人們可以讀出三種不同的歷史意味和生命形態,梁濟的生命形態可謂與傳統全然合一,既帶有倫常的陳腐,又帶有人格的可愛。在此順便說一句,這種迂腐的可愛,後來在其子梁漱溟身上又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了一遍。梁濟是一個真正的文化遺民,其保守其崇高其純樸其貴族,一如當年的伯夷、叔齊。相對於梁濟的這種傳統人格,譚嗣同呈現的卻是一種激進的偉大,譚嗣同的赴義不是伯夷、叔齊式的恪守,而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場景的變相製作,並且被置於同樣的愛國主題,只是在歷史意味上帶有濃厚的進化論色彩。如果說梁濟死於中國文化的道德立場,那麼譚嗣同死於中國歷史所要求的政制變革和社會進步。彼此死在相背,死法各異,然所為者卻一也,即都死於各自懷抱的社會理想和文化觀念。此間唯有抵達了第三種境界的王國維,才死於本真的生命體驗。因為他之於人生之於歷史,不是執政治家之眼觀之,而是就詩人之眼洞察之,得以抵達通古今的深邃高遠,從而死得如同《紅樓夢》中女媧補天那樣始源那樣本真那樣蒼茫渾樸。歷史上,激進的革命家總是不以歷史的詩人之眼為意,儘管他們本身就應該是歷史的詩意,而不是歷史的主人,但他們卻總是樂意扮演主人而不願屈就為詩人。由於這樣的執著,結果使他們在扮演主人的同時變成了觀念的囚徒,由此可以發現的是,譚嗣同之死的焦灼在於其觀念的苦苦折磨。就其理想而言,譚嗣同似乎也通古今,但這不是詩人基於生命之通,而是全然政治型的革命家的基於觀念之通,一者觀念,一者生命,在譚嗣同之死的焦灼和王國維之死的平和之間,僅僅相隔一步之遙。然而恰恰是這麼一步之差,如同大山一般沉重而為世人高不可攀,致使他們從譚嗣同之死中讀出了英雄,卻將王國維之死讀成了遺老殉情之類的流俗齷齪之說。這種猥瑣庸常的閱讀本身,正好標記出了歷史的淪落,也正好證明了王國維在棄世時之所以選擇無言形式的根本原因。正如在歷史面前王國維是清醒的一樣,在死亡面前王國維是智慧的。他的智慧具有老莊式的清靜無為,只是這種智慧在他沒有訴諸《道德經》,也沒有寫成〈逍遙遊〉,而是表述成自沉昆明湖。生命由此抵達了相當審美的涅槃,而且因為涅槃的審美性質,後人可以作出陳寅恪式的解讀,但絕無形成哪門宗教的可能。因為教派一起,生命的審美又會變成觀念的演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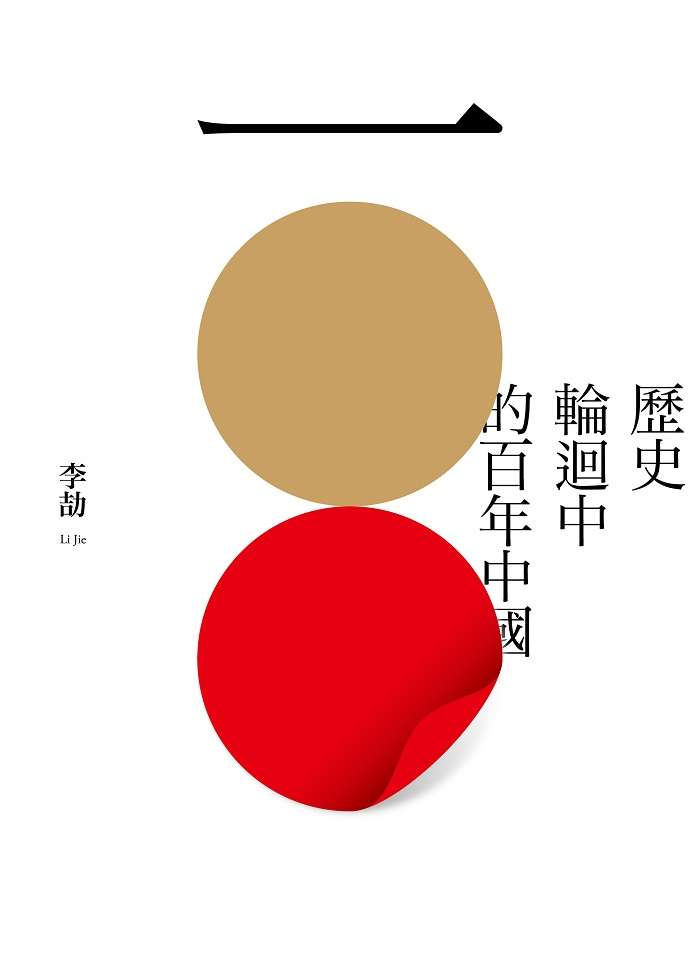
*作者為中國旅美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