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晚近歷史上,也許沒有一個學者獲得過像王國維所獲得的學術成就,沒有一個思想家抵達到像王國維所抵達的高遠境界。
然而,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王國維偏偏又是那麼的缺乏轟轟烈烈之業績,以致他的形象正好應了他的表字靜安,一如他在學術上思想上的對歷史對人生洞若觀火而準確地體現了其號觀堂的觀字。晚近以降,學術大家一般皆有彪炳史冊的事蹟相隨身後,諸如梁啟超之維新,章太炎之入獄,胡適之有白話運動,熊十力有辛亥革命之經歷,如此等等。似乎唯獨王國維一生治學著書,好像默然不聞窗外之事一般。及至最後的為新聞界所關注,卻又不是因為他的驚人之舉,而是他的悄然自沉於昆明湖裡。難怪魯迅會說王國維是個「老實得像火腿一樣」的人。而且我在此想補充一句,此君不僅身前老實如火腿,即使身後也同樣老實如火腿,比如他在甲骨文上的開創性成果,就被一個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文化敗類如同割火腿一般地割去做了鮮美的唯物史觀火腿湯。
當然,上帝畢竟還是公平的,自八○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上對王國維的研究日臻繁榮,即使一些以前立場堅定地痛罵過這位封建遺老的王國維當年的學生,也開始以恭恭敬敬的模樣談論這位學者在學術上具有如何獨特的地位,並且如何平易近人,誨人不倦云云。人們如同過去膜拜魯迅一樣地談論起了這位被歷史風塵所掩沒的人物,並且往往爭先津津樂道於他的某一學術成就,以示自己在這方面的學有所長。只有在說及他的自殺時,他們才變得神色惕然,小心翼翼,全然沒有當年陳寅恪悼輓王國維時的悲痛和共鳴。大陸上的這些所謂的學者教授,包括某些當年王國維教過的學生在內,幾乎沒有一個敢於像陳寅恪那樣正視王國維之死。這些專家談論及梁啟超和戊戌變法可以唾星四濺,一展書生意氣什麼的,但一面對王國維的自沉卻總是那樣的提不起精神。殊不知,要真正進入王國維的精神世界,既不應從他的學術成就開始,也不當從他的政治立場入手,而就是從解讀王國維之死起步。正如讀《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形象必須記住他懸崖撒手的結局,進入王國維精神世界的大門在於他的自沉,從其自沉讀通其思想和人生。因為正如懸崖撒手是賈寶玉形象的精神前提,自沉昆明湖乃是王國維形象的先行規定。
有關王國維自沉,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例舉他的人生困苦,有的例舉他的忠於清室,有的例舉羅振玉對他的影響,有的例舉他所認同的叔本華悲觀哲學,還有的不無深意似地談到當時革命軍北伐的步步進逼,然後舉出王氏死時留下的那紙遣言中的「義無再辱」一說,彷彿其死因不證自明,如此等等。所有這些談論,在我看來可說全都有案可稽,也可說全是無稽之談。說全都成立,是因為他們各自例舉的事因的確全都指向王國維的自沉,諸如歷經幼年喪母、中年亡妻、晚年失子的人生痛苦,生存上的輾轉掙扎,內有續娶的王熙風式的潑辣之妻,外又與朋友羅振玉的失和⋯⋯所有這些具體的因素,正構成了王國維走向昆明湖的一步步足跡,就好比大觀園中的諸多變故連同賈寶玉的頑石脾性之類的種種因素,都是他最終懸崖撒手的成因;但我又說這諸多論說全然無稽,也即是說,王國維的自沉就像賈寶玉的撒手一樣,不是繫在某一個具體因素之上的,而是基於其所有的生存境遇和總體的生命歷程。雖然賈寶玉撒手與林黛玉的夭亡有重大關涉,但誰能斷言賈寶玉就為了林妹妹之死而出家呢?順便說一句,高鶚續作的拙劣也就在於他像後來的眾多專家學者論說王國維之死那樣地理解了賈寶玉的遁入空門。
當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裡將死亡作為先行自身的生存論結構時,他無意間為王國維的自沉和賈寶玉的撒手作出了最為恰當的詮釋:其自沉和撒手的結局先行規定了王國維和賈寶玉的全部生命歷程, 一者是向⋯⋯ 自沉的生存, 一者是向⋯⋯撒手的生存。這也就是說,正如賈寶玉的全部人生歷程可歸結為由色而空的一步步撒手濁世,王國維的整個生命同樣每一步都踏在走向自沉的路途上。就王國維自沉的這種存在論意味而言,在以往對此的全部論說中,唯有陳寅恪的解釋最為接近其本真的死因。寅恪先生在他的〈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寫道: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齣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據說有位海外學者根據陳寅恪之於王國維之死的如此追悼,將王國維連同陳寅恪一起稱作「文化遺民」。我不知這位學者在這文化遺民一說上作如何闡釋,但遺民的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自伯夷、叔齊以來,遺民在中國知識分子是作為一種傳統形成的,並且歷經數千年而不衰,宋亡有宋末遺民,明亡有明末遺民。然文化遺民之於過去的遺民傳統則又大不相同,因其不是執著於某個王朝而是執著於整個文化。如果說伯夷、叔齊式的遺民所恪守的是某個種姓的王朝或某種倫理秩序和社會結構,那麼王國維作為一個文化遺民所體現的則是一種歷史的本真精神。歷史無論再進化,文化卻具有天然的恒常性。當王國維如同陳寅恪所說的那樣凝聚了整個文化精神之後,他的生命之於歷史便有了超常的意味。在此,生命的空間性消解了生命所置身的歷史的時間性。也即是說,生命之於文化精神的凝聚,使王國維這樣的歷史人物不再僅僅是語言芬芳的感受者,而且他的存在就是芬芳本身。所謂文化遺民,不過相對歷史的進化或歷史的更迭而言,就文化本身而言,王國維恰好是存在本身的象徵。王國維的自沉不是被歷史的遺棄,而是其生命以拒絕指認的高貴姿態遺棄了一部可疑的歷史。這裡的關鍵不在於被動的遺棄,而是在於主動將濁世從自身的生命中整個地拋了出去。因為生命臨世可能呈現為被拋的,但生命的棄世在生命卻是主動的拋出。在這裡,重要的是生命的能否拒絕。賈寶玉拒絕了對整個家族興衰的承擔,王國維拒絕了對整個歷史衰敗的認可;最後陳寅恪由此省悟,以壁立千仞的姿態拒絕了對這種歷史景觀的苛同。這樣的拒絕能力既可標明生者與死者的相通,也可劃分死者與死者的區別。

在王國維自沉面前領悟最深的陳寅恪,其整個生命就因為這樣的領悟而被王國維之死點亮。早年陳寅恪尚存河汾之志,胸懷經世之學。儘管他早就看出中國歷史在審美向度上的闕如,在致友的信中指出「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實用,不究虛理。」但他同時又認為:「而救國濟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也即是說,他一方面看出先秦以後以孔孟為基調的中國文化的不究虛理,一方面又把虛理看作是救國濟世的根基。及至王國維自沉,他才恍然大悟:虛理與濟世並不全然一致,文化精神並非與歷史進程並行不悖。由此,他認領了自己的文化角色,不再志在河汾,而是壁立千仞。以著述《柳如是別傳》了卻餘生。好比《紅樓夢》從大觀園女兒世界揭示了整個歷史的淪喪一樣,《柳如是別傳》經由對一部明末清初王朝興衰異族侵伐的歷史的悉心考察,寫出了一個身為下賤心比天高的才情並茂的燦爛女子。《資治通鑑》式的歷史風雲,在柳如是這樣的女子面前全都成為陪襯的背景。陳寅恪以此如同《紅樓夢》那樣為歷史確立了審美向度,其意味又一如王國維的自沉為一部行將迷失的歷史樹立了空谷跫音般的文化精神。陳寅恪沒有像王國維那樣自殺,但他晚年所致力於的鉅著《柳如是別傳》卻獲得了與王國維之死同樣的精神芬芳。
與這種生者與死者的相通相反,與王國維差不多相同時期的梁濟之死卻沒有獲得與王國維全然相同的意味。梁濟的品性不在伯夷、叔齊之下,其文化人格也為同時代的許多文化人所不可比肩。他的自殺表明了一種真正的遺民秉性,在生命的自擇和自覺上幾乎與慷慨赴義的譚嗣同相近。然而,梁濟死得太明確。他在他一再表白的洋洋數萬言的遺書中將其自殺的濟世意味闡說得清清楚楚。梁濟赴義的英勇令人欽佩,更毋需說其中蘊含的耿直和剛烈,但遺憾的是,他的智慧還不曾抵達真理的無言境界。本真的文化精神如同生命的真理,乃是無以言說的;王國維自沉式的自覺性不在於在死亡面前的宣言,而在於在死亡面前的沉默。正如生命的被拋是無聲的,生命的棄世也同樣是無言的。相對於王國維死得天然,梁濟死得充滿戲劇性,如同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李爾王那樣向世人朗誦了一段段長長的內心獨白。作為一種品性或人格,這無疑也是高尚的,足以令人肅然起敬,但作為文化精神、作為本真的真理,過多的告白卻沖淡了真理的本真意味。語言的芬芳之於感受者,不在於言說,而在於心領神會。王國維之於他的自沉,幾乎不著一字,但領略如陳寅恪者便領略了,而不領略如眾多庸常文人政客者也就不領略了。
生命之於歷史的真正拒絕就是無言的,如《紅樓夢》,如王國維,如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也正因為這樣的無言,使拒絕本身構成了歷史的向度乃至歷史本身。因為《紅樓夢》的存在,因為王國維的自沉,因為《柳如是別傳》,在人們說歷史是帝王將相的歷史、農民起義的歷史、改良開放的歷史、科學民主的歷史的同時,我們同樣可以說還有生命本真的歷史,文化精神的歷史。語言並不是歷史的真正主宰,暴力也不是歷史唯一的動因,在歷史的衰敗時期,無言的拒絕構成了對衰敗最為根本的終極批判。
與洞若觀火的王國維相比,梁濟之於歷史總有點隔霧看花,從而就感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文化倫常立場指斥歷史的衰敗。這樣的儒生意氣,頗近於林紓,但有別於王國維。作為歷史的終極批判,王國維的自沉觸摸到了歷史的根本癥結,亦即陳寅恪曾隱約所見的中國歷史之於審美精神的缺乏。當王國維感慨「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感慨中國文化中「美術之無獨立價值也久矣」的時候,他所洞見的乃是文化命脈自周秦以後的某種殘缺及其由此殘缺而導致的式微。當王國維指出西方的哲學思想分為「可愛而不可信,可信而不可愛」二種類型時,他所發現的是這二種哲學之於中國文化的共同闕如。因為在先秦以降的中國文化體系中,既沒有「可愛而不可信」的純粹哲學和純粹美學,也沒有「可信而不可愛」的理性邏輯和實證科學。

基於文化的這種巨大空缺,王國維選擇了無言的自沉,一如賈寶玉基於以女神、愛神、詩魂林黛玉及其大觀園女兒世界為標記的生命和真理的的泯滅和失落,最終懸崖撒手,將一個沒有愛和歡笑的世界連同一部沒有審美向度的歷史一起從他的生命中拋了出去。然而,又正是這樣的自沉和這樣的撒手,為歷史確立了存在的維度,從而向一個殘破的文化空間注入了本真的生命元氣。就這樣的意義而言,王國維的自沉和賈寶玉的撒手,與《紅樓夢》開卷所描述的女媧煉石補天具有同樣的歷史文化意味。或者可以說,王國維和賈寶玉一樣,乃是女媧所煉之石,只是賈寶玉作為一塊頑石是由以林妹妹為首的大觀園女兒們的淚水所洗淨,從而成道為玉的;而王國維作為一個蓋世學者則是由他自己的悟性和在這悟性導引下的著述完成生命的修煉和昇華,最後以自沉的方式將生命停格為歷史的審美向度和文化精神的本真維度。在此,生命作為一種人世的生存體驗是苦痛的,但作為對這種苦痛的直面又是有境界的,因為生命藉此,在一部害怕悲劇、規避悲劇以掩飾這種規避背後對生命的種種屠戮的既殘忍又虛偽的歷史中,開啟了悲劇的序幕,並且在開啟方式上選擇了無言的古雅形式。
相比於梁濟的敬告世人和譚嗣同的慷慨就義,王國維的自沉方式呈現出更為純粹的非功利的審美氣度。這樣的氣度印證了他在文學藝術上的非功利的「遊戲說」,即「文學、美術不過成人精神的遊戲」,而這種遊戲的根本意味也就在於其純粹的審美。基於這樣的審美立場,王國維的自沉連同其艱難困苦的人生旅程不是事功的、濟世的,也不是體現獨善其身之生存策略的,而是藝術的、審美的、體驗的。如果說悲劇意味著一種巨大的審美快感的話,那麼王國維的自沉則正好是這種快感的全身心的體驗。由於如此深入的生命體驗,王國維走向昆明湖的腳步並不像人們通常想像的那麼沉重那麼淒慘,而具有一般人所無法想像的平靜和愉快。因為這腳步即沒有「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式的迷惘,也沒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焦灼,從而全然洋溢著「夢裡尋他千百度,回首驀見,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欣喜和恬然。相形之下,梁濟死得迷惘,譚嗣同死得焦灼,唯有王國維死得寧靜,宛如一味淡淡的清香,在投水的一刹那從昆明湖上飄散開去,縈迴於天地之間,觀照出人世的苦難,觀照出歷史的劫變。遺憾的只是,當時的呼吸領會者,獨寅恪而已。
從上述三種不同的赴死境界上,人們可以讀出三種不同的歷史意味和生命形態,梁濟的生命形態可謂與傳統全然合一,既帶有倫常的陳腐,又帶有人格的可愛。在此順便說一句,這種迂腐的可愛,後來在其子梁漱溟身上又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了一遍。梁濟是一個真正的文化遺民,其保守其崇高其純樸其貴族,一如當年的伯夷、叔齊。相對於梁濟的這種傳統人格,譚嗣同呈現的卻是一種激進的偉大,譚嗣同的赴義不是伯夷、叔齊式的恪守,而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場景的變相製作,並且被置於同樣的愛國主題,只是在歷史意味上帶有濃厚的進化論色彩。如果說梁濟死於中國文化的道德立場,那麼譚嗣同死於中國歷史所要求的政制變革和社會進步。彼此死在相背,死法各異,然所為者卻一也,即都死於各自懷抱的社會理想和文化觀念。此間唯有抵達了第三種境界的王國維,才死於本真的生命體驗。因為他之於人生之於歷史,不是執政治家之眼觀之,而是就詩人之眼洞察之,得以抵達通古今的深邃高遠,從而死得如同《紅樓夢》中女媧補天那樣始源那樣本真那樣蒼茫渾樸。歷史上,激進的革命家總是不以歷史的詩人之眼為意,儘管他們本身就應該是歷史的詩意,而不是歷史的主人,但他們卻總是樂意扮演主人而不願屈就為詩人。由於這樣的執著,結果使他們在扮演主人的同時變成了觀念的囚徒,由此可以發現的是,譚嗣同之死的焦灼在於其觀念的苦苦折磨。就其理想而言,譚嗣同似乎也通古今,但這不是詩人基於生命之通,而是全然政治型的革命家的基於觀念之通,一者觀念,一者生命,在譚嗣同之死的焦灼和王國維之死的平和之間,僅僅相隔一步之遙。然而恰恰是這麼一步之差,如同大山一般沉重而為世人高不可攀,致使他們從譚嗣同之死中讀出了英雄,卻將王國維之死讀成了遺老殉情之類的流俗齷齪之說。這種猥瑣庸常的閱讀本身,正好標記出了歷史的淪落,也正好證明了王國維在棄世時之所以選擇無言形式的根本原因。正如在歷史面前王國維是清醒的一樣,在死亡面前王國維是智慧的。他的智慧具有老莊式的清靜無為,只是這種智慧在他沒有訴諸《道德經》,也沒有寫成〈逍遙遊〉,而是表述成自沉昆明湖。生命由此抵達了相當審美的涅槃,而且因為涅槃的審美性質,後人可以作出陳寅恪式的解讀,但絕無形成哪門宗教的可能。因為教派一起,生命的審美又會變成觀念的演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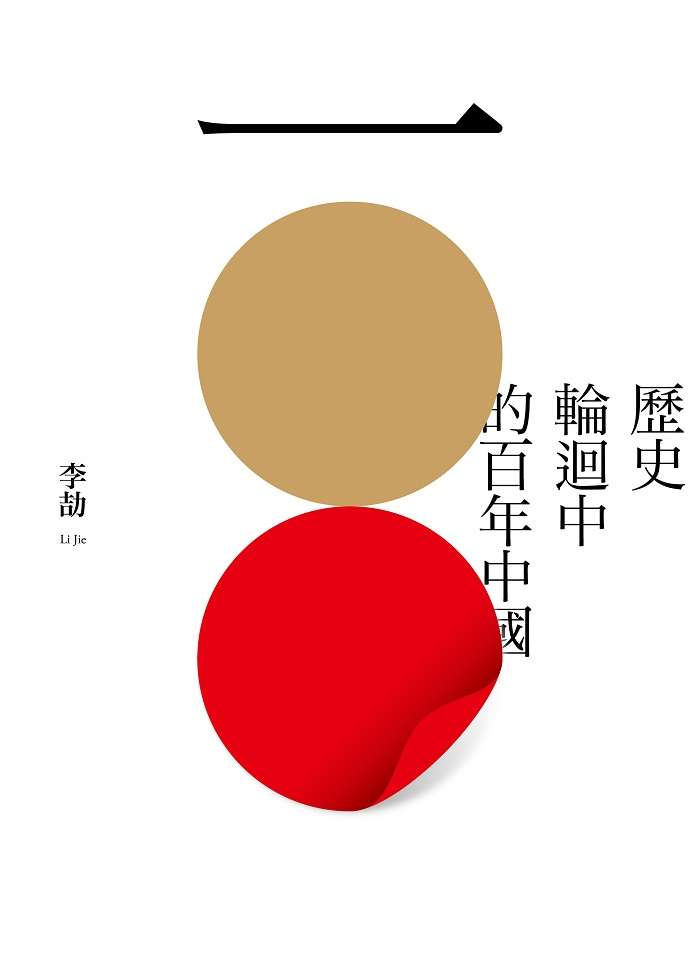
*作者為中國旅美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