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代,我以科技生活為題訪問的孩子,常邊寫作業邊看電視或聽音樂,還有掌上型電玩分散注意力,代數和超級瑪利歐同在一起。今天,這樣的回憶聽來洋溢田園風情。現在的孩子通常一邊寫作業,一邊上臉書、購物、聽音樂、玩線上遊戲、傳簡訊、看影片、講電話和打即時通等等。唯一缺席的是電子郵件: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多半認為這是過去的技術,或許在申請大學或應徵工作的時候才用得上。
微妙的是,隨時間過去,曾看似某種禍害的一心多用,已被重塑為一種美德。隨時間過去,我們已無必要討論一心多用的優點,因為年輕人已因有辦法同時處理許多事務而備受肯定。專家甚至宣稱一心多用不僅是種技能,更是在數位文化中順利工作及學習的關鍵技能。甚至有人擔心一次只能做一件事的老派教師會妨礙學生學習。現在我們必須了解我們有多容易受虐,當心理學家研究一心多用時,他們沒有發現效率被去舊換新的故事;一心多用的人嘗試執行的每一件任務,表現都沒那麼好。但一心多用感覺良好,因為身體會分泌誘發「興奮感」的神經化學物質來獎勵它。這種興奮感會騙使一心多用者以為自己特別有生產力。為追求這種快感,他們還想做更多事。未來的日子,會有很多物事需要釐清:我們愛上那些被科技弄得簡單的東西,我們的身體是共犯。
現今,當一些教育者試圖將智慧型手機與教室整合之際,也有教師試著禁用媒體來讓學生專心做正事。在我任教的大學教授分成兩派,對於該不該干涉各持己見。有些教授說,我們的學生都是大人了,我們沒必要規定他們怎麼作筆記,或在他們的心思飄離課程相關資料時要他們專心。但當我站在我們有Wi-Fi 的演講廳後方,學生都在看臉書和YouTube、還上網購物(主要是音樂)時,我希望我的學生參與對話,我不認為他們該用課堂時間做其他事情。有一年,我提出這個主題做總討論,並建議用筆記本(紙的那種)來寫筆記。一些學生說他們如釋重負,「現在我不會受到臉書訊息誘惑了,」一個大二學生說。其他學生則很不高興,幾乎惱羞成怒。他們沒立場捍衛在課堂上購物和下載音樂的權利,所以堅持說他們喜歡用電腦做筆記。我強迫他們用手寫,之後再鍵入電腦文件。雖然他們對這「多此一舉」怨聲載道,但我暗自思忖這或許是不錯的學習策略。我維持我的決定,但次年我便順應潮流,允許學生做他們想做的事,最後我和幾個同事都發現,上課打開筆記型電腦的學生,成績沒有其他學生好。

當媒體一直在那裡、等著被需要時,人們便失去選擇通訊的意識。用智慧型手機的人談到看著他們的人生「捲動」何其心醉神迷,看著自己的人生就像觀賞一部電影。一個人說:「我看我的手錶來獲知時間;我看我的黑莓機來感覺我的人生。」成年人承認打斷工作查看電子郵件和訊息會使他們分心,但也表示他們絕對不會放手。當我特別問青少年寫作業時被打斷的事(例如被臉書訊息或新的簡訊打斷),很多人似乎不了解問題。他們的回答不脫「本來就是這樣啊,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啊」之類的。當黑莓機版的人生電影變成真正的人生,會產生一個問題:黑莓機的版本是未編輯過的人生版本,它涵蓋的內容不是一個人所擁有的時間可以負荷的。我們雖然追不上,卻覺得要為它負責,那畢竟是我們的人生。我們努力成為那個追得上電子郵件的自我。
我們的網路裝置鼓勵一種新的時間觀念:它們保證可以讓你堆疊更多活動上去,因為你可以一邊做其他事情一邊傳簡訊,簡訊看起來不會占用時間,反而會給你時間。這大受歡迎、太神奇了,我們終於設法擠出一點額外的時間,但我們之中生活步調最快的人,卻鼓勵我們去讀《愛上慢活》(In Praise of Slowness)之類的書。而我們總算找到多點時間陪家人朋友,雖然我們的注意力甚少在他們身上。
兩代之間的問題叫人不知所措。青少年抱怨爸媽晚餐時眼睛一直盯著手機不抬起來,也帶著電話參與他們的學校體育活動。十六歲的漢娜是個嚴肅、安靜的高二學生,她告訴我多年來她一直試著在母親來接她放學或下舞蹈課時吸引母親注意,漢娜說:「車子開動後,她會一邊開車一邊低頭看她的訊息,連一句哈囉都沒有。」後面我們將會聽到其他人說類似的故事。
爸媽說他們對這種行為深感羞愧,但隨即找機會解釋,或自圓其說。他們說他們的壓力比以往來得大,不得不追著電子郵件和訊息跑。他們總是有落後的感覺。他們不把公事帶在身上沒辦法度假,而他們的辦公室就在手機上。他們抱怨雇主要他們一直保持連線,但又坦承他們花在通訊裝置的心力已超過所有工作上的期望。
青少年一旦時間緊迫(該交作業了),可能會試圖逃離不關機文化的要求。有些人會用爸媽的帳號,這樣朋友就不知道他們在線上。成人也會躲藏,周末時行動裝置會留在辦公室或上鎖的抽屜,如果雇主要求聯繫,人們就實行規避策略,他們會去過冒險假期或從事極限運動。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仍可能搭乘沒有手機或網路存取的長途班機。但就連這點也在變。Wi-Fi 已經上天空了。
在一個被拴住的世界,太多事是有可能的,但很少人能夠抗拒不用這樣的基準來衡量成就:如果隨時隨地都可以工作,可能完成多少事情。三十六歲的黛安是中西部一間大型博物館的館長,她跟不上科技所設定的步調。
我已經想不起來前一次有週末這種東西,或拿到一本萬用手冊、想想可以把誰的名字加進通訊錄是什麼時候了。我的電子郵件程式讓我只要點選寫信給我的發信人,然後,咻的一聲,他就在我通訊錄裡了。現在每一個寫信給我的人都在我的通訊錄裡;每個人都是準聯絡人、準買家、準捐贈者、準籌款人。以前是通訊錄的東西,現在更像資料庫了。
我想我的工作是有做得比較好,但工作成了我全部的生活;或者我全部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當我從行事曆移往通訊錄、再移往電子郵件、移往簡訊,我覺得自己好像太空超人,每件事都如此有效率。我是一部效率極高的機器。我直到凌晨兩點都還在黑莓機上。我睡不好,但仍趕不上一直寄給我的信。
現在為了工作,我應該要有代表博物館的推特和臉書。要開部落格寫博物館發生的事,那意味我得不停上網。我的聲音出了狀況,我一直在失聲中,那不是講太多話所致,我所做的就只有打字,但那卻傷了我的聲帶。醫生說那是緊張造成的。
與許多程式為伍的黛安覺得自己像「太空超人」,但她的力量僅堪成為一部「效率極高的機器」,專門回應網路扔給她的東西。她和丈夫決定兩人該去度個假。黛安打算告訴同事她要「離線」兩個星期,但一直沒說出口,她不知該如何啟齒。那間博物館的規矩是休假度假沒問題,但度假期間不可離線。因此,度假通常意味著在某個風景如畫的地方工作。事實上,無線網路的廣告就常凸顯帥哥美女徜徉海灘的畫面。被拴住的我們不會否定身體和它的樂趣,但會把身體放在某個漂亮的地方,一邊工作。曾經,行動裝置需要在這樣的廣告裡展示,現在多半則是用暗示。我們知道成功人士永不斷線,度假的意思是離開一個地方,而非脫離一連串的責任。在一個不斷通訊的世界,黛安的症狀看來相當契合:她已經變成通訊的機器,卻一點聲音也沒留給自己。
當黛安計畫她的「離線度假」時,她坦承自己其實想去巴黎,「但在巴黎就沒有不上線的藉口了。去亞馬遜流域協助建屋,嗯,誰會知道那裡有沒有Wi-Fi ?關於度假地點,我有個無可談判的新條件:我必須至少能假裝那裡沒有帶電腦去的理由。」但在她遙遠的巴西假期終於成行後,她告訴我,「每個人都帶黑莓機坐在帳篷裡,黑莓機都開著。好像天空裡停泊著某顆巨大的人造衛星似的。」
黛安說她一天大約收到五百封電子郵件、數百則簡訊和大約四十通電話。她指出,很多商業訊息都是多管齊下的:人們先傳簡訊和電子郵件,然後打電話、在她的語音信箱留言。「客戶很焦慮,」她解釋說:「要不斷聯繫,他們才比較有安全感。」在她的世界,黛安習慣收到匆忙的訊息,她也會迅速回信。她擔心她沒有時間不慌不忙地處理重要的事務。
而在不斷聯繫的嘈雜聲中,也很難維持辨別輕重緩急的判斷力。在這個迅速回應的世界裡塑造的自我,會以打電話的次數、回覆的郵件和簡訊數、完成的聯絡數來衡量成就。這個自我是以科技提出的基準、透過科技簡化的事物來進行校正。但在科技所造成追求數量和速度的壓力中,我們面臨了一個矛盾。大家都說我們的世界愈來愈複雜,但我們創造的通訊文化偏偏減少了我們可以坐下來、不受干擾地思考的時間。隨著我們以要求即時回應的方式通訊,我們並沒有足夠的空間來思考複雜的問題。
四十六歲的特瑞是波士頓一家大型事務所的律師,他明確提出這個議題。他在電子郵件上說:「我回答可以即刻回答的問題,人們也希望我馬上回答問題。但不僅是速度……那些問題已經改成我可以馬上回答的問題了。」特瑞說法律事務常需要時間和細微的東西,但「現在的人沒有那種耐心了。他們會寫信,然後預期很快得到回覆。他們願意放棄那些細微的東西;真的,顧客想馬上就聽到東西,所以我都給在信裡就能回的答覆……或者最多會花我一天的答覆……我不得不做粗枝大葉的思考。」他改口:「當然,這不是科技造成的,但科技設定了關於速度的期待。」我們回到關於預設用途和人性脆弱的問題。科技賦予我們速度,而頭昏腦脹的我們很高興有科技幫助我們加快速度。特瑞提醒我:「我們靠『發射』(shooting off)電郵來交談。但沒有人會因為想讓事情盡速進行就亂『發射』(shoots something off)東西的。」
一如黛安,特瑞亦指出客戶常傳簡訊和電子郵件給他,又在語音信箱裡留言。「他們是在說:『餵我。』他們自認有這種權利。」他總結了過去十年的經驗。電子通訊帶來自由,但到最後,「它讓我上了速度愈來愈快的跑步機,但那跟有效率是兩碼子事。」
我和一群律師聊過,他們全都認為沒有「手機」,他們就沒辦法工作—這句話幾乎是對當今智慧型手機普世一致的簡評,那不只擁有了桌上型電腦的許多功能,而且還有更多功用。律師們堅稱行動裝置使他們更有效率,也「解放」了他們,讓他們可以在家工作和跟家人出遊。
女性尤其強調網路生活讓她們得以保住工作和有時間陪小孩。不過,她們也說行動裝置吃掉了她們的思考時間。一人說:「我沒有足夠的時間跟我的心靈獨處。」其他人說:「我得努力掙出更多時間思考。」「我刻意抽出時間思考。」「我得事先規劃思考的時間。」這些說法都仰賴一個在想像中與科技分開的「我」,一個能夠把科技撇在一旁、以便獨立運作的自我。這與一個日益普遍的現象形成對比:我們過著螢幕不滅的生活。這個事實讓我們如同MIT 的賽柏格,學會把自己看作和我們的裝置結為一體。抽出更多時間思考代表要關掉手機,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今天我們的裝置已經比以往更貼近我們的身體和心靈。它們提供了社交和心理上的GPS,一種給被拴住的自我使用的導航系統。
至於黛安,她在以往的「工作空檔」—搭計程車或排隊等候或走路上班期間,那些可以拿來做白日夢的時間—仍努力繼續通訊。這或許是我們(身體和情緒)要維持專注力所需的時間,但黛安不允許自己這麼做。當然,她運用的是我們新的時間類型:注意力分享(attention sharing)的時刻。
黛安盡量不接電話,因為電話的實時性需求會占用她太多的注意力。但就像電話代替的面對面互動,電話也能以簡訊和電子郵件辦不到的方式傳達事情。所有當事人都在場,如有問題可當場回答,人們可以表達混雜的情感。反觀電子郵件就經常來回數次而沒解決事情,誤解屢見不鮮。感覺會受傷,而誤解愈深電子郵件往來的數量就愈多,這毫無必要。我們開始覺得收件匣裡那一整列未讀取的訊息是個負擔,然後,我們會投射我們的感覺,唯恐我們的訊息也成了他人的負擔。
我們確實有道理擔心。我一個朋友就曾在臉書發文:「處理堆積郵件的問題在於,你一回覆郵件,人們也會回你!所以你每處理十封,就會再收到五封!我的目標是今晚剩三百封,明天一百封。」這已成為相當普遍的感嘆。但聽到自己用「待處理」或「已擺脫」等平常談論垃圾的語言來形容朋友的信,是滿悲哀的事。但這就是我們用的語言。
每一封電子郵件或訊息似乎都在前往垃圾桶的路上。今天,隨著綿延不斷的簡訊流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或許會對彼此少說些話,因為我們想像,我們所說的話十之八九會被當成垃圾。天生為電文體的簡訊,當然可以情感豐沛、具洞察力而性感,可以使我們精神為之一振,可以讓我們覺得被理解、被欲望和被支持。但簡訊不是深入理解一個問題、或解釋複雜情勢的地方。簡訊是動量,只能填補一個時刻。

可怕的對稱
當我說到一種新的自我狀態,無生命的自己時,我用「itself」這個詞是有用意的。雖然有點誇飾,但這個詞如實呈現了我的憂慮:連線的生活鼓勵我們用類似處理物品的方式,迅捷有效地對待我們在線上遇到的人。一切是那麼自然:當你被成千上萬、多於你所能回應的電子郵件、簡訊和訊息圍攻,需求便失去人性了。同樣地,當我們在推特發文,或把數百或數千名「臉友」當成一個群組來寫東西時,也是把個體視為一個單位—朋友成了粉絲。一個大三學生仔細回想自己可在網上聯絡到的群眾時表示:「我覺得我是一個龐大東西的一部分,網路與世界在我眼中成了一樣東西,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也是,我不再把他們視為個體,他們也是這個大東西的一部分。」
對於社交機器人,我們是把物體想像成人。在網路上,我們則發明了新的人際相處方式:把人轉化成類似物體的東西。把人視為東西對待的自我,很容易把自己也當成東西。還記得嗎?當我們認為機器人對我們而言「夠像有生命的」時,我們是在拔擢它們;如果在網路上,人們覺得只是「有足夠生命」以處理為電子郵件和訊息的「極高效率的機器」,那人就是被降等了。這就是可怕的對稱。
在本書第一部分,我們見到與機器人的新連結讓我們開始渴望無交流可言的交流。無獨有偶,本書第二部分所追蹤的弧線,終點也是支離破碎的交流。我們在線上的親密關係中取暖,盼能獲得同情,卻往往獲得陌生人的殘酷。在我探索網路生活以及它對親密與孤獨、對身分認同和隱私的影響時,我會敘述許多成年人的經歷。有特定幾章幾乎完全著眼於成人,但我也會一再回到青少年的世界。今天的青少年是跟社交機器人一起長大的。他們的成長過程也有網路陪伴,有些早從八歲就拿到第一支手機了。他們的故事清楚顯示科技是如何重新塑造身分認同,因為身分認同正是青少年生活的核心要件。透過他們的眼睛,我們看到一種新的感性逐漸顯露。
今天,文化規範正迅速變遷。以往,我們常將成長與獨立運作的能力畫上等號;現今,永不斷線的連結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善於合作的自我有何優點。如果,日復一日,我們連孤獨時都在一起,那麼一切有關獨立自主的問題,面貌將截然不同。
網路對現今年輕人的影響很難論斷是非。網路連線便於玩弄身分(例如試驗一個和你迥異的分身),卻更難拋開過去,因為網際網路永遠存在。
網路使分離變得容易(手機給予孩子更大的自由)卻也約束了分離(爸媽隨時可打電話給他)。青少年迴避電話的「即時性」要求,消失在他們形容為「社群」和「世界」的角色扮演遊戲中。然而,正當他們投入乙太的新生活,很多人卻表現出意想不到的懷舊。他們開始怨恨強迫使用他們個人檔案的裝置;他們渴望個人資訊不會像做生意要付出的成本那樣被自動取走。通常是孩子要爸媽在晚飯時把手機收起來,是年輕人開始談論在他們眼中,他們的長輩已然屈從的問題。
十六歲的桑傑接受我的訪問。我們要利用他的午休時間聊一個小時。對話開始時,他從口袋拿出手機關掉。 對話結束,他把手機打開。他可憐兮兮、難掩尷尬地看著我。在我們說話的同時,他收到上百則文字訊息。有些傳自他的女友,他說她正「大發雷霆」。有些則傳自一群摯友,他們打算辦一場小型音樂會。他覺得非回不可,於是開始收拾書本和筆電,打算找個安靜的地方定下來做這件事。說再見的時候,他補充一句—不是特別對著我說、更像對他自己說,像是對我們這段對話的心得:「我無法想像等我大一點還會做這種事,」然後,他小聲地接下去:「這種事我還得繼續做多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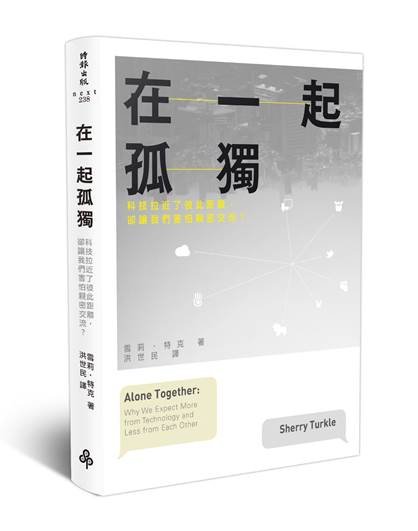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在一起孤獨》一書;作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現居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MIT)科技社會研究教授,MIT科技和自我創新計畫(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創辦人兼主任,也是有執照的臨床心理學家。投身科技心理研究超過三十年,被凱文.凱利譽為科技界的佛洛伊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