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胡適在《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的序中,就曾指出:「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而影響及於全國。」張謇是中國近代實業家、教育家。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清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時值中日甲午戰爭新敗,鑑於當時政治革新無望,他決心投身興辦實業和教育。
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在南通開始創辦大生紗廠。後又舉辦通海墾牧公司、大達輪船公司、復新麵粉公司、資生鐵冶公司、淮海實業銀行等企業,並投資江蘇省鐵路公司、大生輪船公司、鎮江大照電燈廠等企業。並先後創辦通州師範學校、南通博物苑、女紅傳習所等。他認為實業、教育才是一國「富強之大本」。他曾參與發起立憲運動,光緒三十二年(1906)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宣統元年(1909)被推為江蘇諮議局議長,為清末立憲運動主要代表之一。
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總長但並未就職,他擁護袁世凱,並組織統一黨與國民黨對抗。一九一三年任袁政府農商總長,一九一五年因不滿袁世凱公然恢復帝制,始辭職南歸。在南通繼續辦理實業和教育,提倡尊孔讀經,抵制新文化運動。一九二五年大生紗廠因虧損嚴重被接管,次年八月病逝。著有《張季子九錄》、《張謇函稿》、《張謇日記》、《嗇翁自訂年譜》等。

張謇出身農家,祖父上一輩都沒有讀過書。父親也是稍微讀過點書而已。他五歲開始上學,塾師見門外有人騎白馬,便寫出「人騎白馬門前過」的上聯,讓學生對下聯。張謇應聲對道:「我踏金鰲海上來!」老師大喜,父親也很高興,認為此子口氣很大,將來一定成材。同治八年(1869),十六歲的張謇果然考中秀才。
清代的科舉考試,沿襲明制。一個讀書人要中狀元,起碼要經過三重考試,俗稱「三考出身」。先由童生(凡讀書人往應縣試時,皆稱童生或生童、文童,與年紀無關,因此有八十老童生。)去應縣試,由知縣做考官,考取後,再應府試,由知府為主考,中後就是秀才了。有了秀才的資格,就可以到省城去考舉人, 張謇從中秀才起,中經同治十一年(1871)、同治十三年(1874)、光緒二年(1876)、光緒三年(1877)、光緒六年(1880)前後五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舉人考試),可是都沒有考取。
同治十三年(1874),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從事公文寫抄工作。從此,張謇開始了旅幕生涯。光緒二年(1876)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光緒六年(1880)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朝鮮發生「壬午兵變」,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由此受到「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在朝鮮,張謇「理畫前敵軍事」的能力和他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的雄文,使得朝鮮方面要以「賓師」的待遇挽留他。在國內,李鴻章等大臣也要推薦他到朝中當官,但張謇謝絕了,他要回國,他要走「金榜題名」的從政道路。光緒十年(1884)吳長慶奉調回國,不久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光緒十一年(1885),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於是張謇轉赴順天鄉試(俗稱北闈),時任工部尚書的翁同龢對張謇的此次考試,十分關心,並親往城東單牌樓觀音寺胡同文昌觀音廟,訪問借宿在那裡的老同鄉張謇,問寒問暖,關懷備至。十月十八日鄉試出榜,張謇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實際上是南方各省的第一名,因為第一名舉人「解元」,必須是直隸人。)。而此次的「解元」是直隸鹽山人劉若曾,他和張謇一同成為鄉試主考翁同龢的得意門生。張謇並代此次主考官潘祖蔭、翁同龢撰〈乙酉順天鄉試錄前、後敘〉,據學者都樾文章(註一)說:「據《翁同龢日記》記載:十月十三日『張季直來,以〈後敘〉託之。』張謇於十八日『為常熟師作〈鄉試錄後序〉』,二十三日『為潘師作〈鄉試錄前序〉』」。
張謇中了舉人後,他就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層次進發。光緒十二年(1886)張謇應禮部會試不中,據學者都樾文章(註二)說:「四月二十九日張謇和劉若曾、朱銘盤一同出都返鄉。而在張謇落榜後,翁同龢曾於四月十三日親到張謇寓所拜訪,所談皆披露膽之言。」
光緒十五年(1889)張謇再赴禮部會試,根據張謇之子孝若所作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記載:「光緒十五年我父親三十七歲的會試,總裁是潘公(按:潘祖蔭),他滿意要中我父,那曉得無端誤中無錫的孫叔和,當時懊喪得了不得。」光緒十六年(1890)是慶賀光緒帝親政而加開的恩科(按:三年一試乃正科,如果今年已有科考,但明年碰到國家有什麼慶典,或皇帝六十大壽之類,就加開一科,故名恩科。)張謇再赴禮部會試,根據《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記載:「到了第二年光緒十六年的會試,房考是雲南高蔚光,曾經將我父的卷子薦上去,場中又誤以陶世鳳的卷子當做我父的,中了陶的會元(按:貢士第一名)。
等到翁公(按:翁同龢)曉得弄錯了,竭力留我父考學正官,我父不願在京久住,就回南邊了。」是科正總裁是孫毓汶,時任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是「后黨」的中堅人物。當時已經置身「清流」的張謇就曾批評說:「自恭王去,醇王執政,孫毓汶擅權,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問,……故談朝局國變者,謂始於甲申也!」因此張謇在探知闈中閱卷實情後在四月十二日的日記無奈自我解嘲說:「知堂批出孫毓汶,二人(按:孫毓汶和高蔚光)素不為清議所齒,得失無傷也。」雖是如此,但張謇應該有寫信給翁同龢表達憤憤之情,張謇自訂年譜云:「翁尚書命留試學正官,非余意,久於京無力。謝歸。」
當時翁同龢兼任管理國子監事務大臣,因此要張謇留京參加學正考試,但張謇沒有接受。四月二十日的日記云:「常熟師(按:翁同龢)贐以二十金,許為覓一書院,留試學正,不能從也。」張謇引起翁同龢的關注在光緒十一年獲中舉人,兩人知遇頗深。此後張謇參加會試卻屢屢受挫,翁同龢始終對其寄寓關心和同情。在這次張謇落第後,翁同龢就曾致函張謇說:「竊為國家惜,非為諸君惜也」,表達了為國家遺失人才的惋惜之情。

光緒十八年(1892)張謇第四度參加禮部會試,根據《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記載:「到了光緒十八年我父四十歲的會試,錯得越發曲折離奇了。當時場闈中的總裁房考,幾乎沒有一個不尋覓我父的卷子(註三)。翁公在江蘇卷子上堂的時候,沒有一刻不告訴同考的人要細心校閱。先得到袁公爽秋所薦的施啟宇的卷子,袁公說:『像是有點像,但是不一定拿得穩。』等到看見內中有『聲氣潛通於宮掖』的句子,更游移起來。後來四川人施某(按:施紀雲)薦劉可毅的卷子,翁公起初也很懷疑;但是既不能確定我父的卷子是那一本,所以施某竭力說:『這確是張季直的卷子。』翁公也有點相信起來,而且看到策問第四篇中間,有『歷箕子之封』的句子,更證實了這是到過高麗的人的口氣;就立刻問袁公,袁公覺得文氣跳蕩,恐怕有點不對。填榜的前頭,沈公子封要求看一看卷子;等看到內中的制藝,及詩秦等韻,就竭力說:『決定不是。』但到了這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到拆封的時候,在紅號內,方才曉得是常州劉可毅的卷子,果然不是我父的。於是翁公、孫公家鼐、沈公大家四處找我父的卷子,方才曉得在第三房馮金鑑那裡。第一房是朱桂卿,第二房是袁爽秋;堂薦送江蘇卷子的時候,朱已因病撤任,袁公和馮金鑑住在隔房,常常叮囑他,遇到江蘇的卷子,要格外留心,不要大意。那曉得馮吃鴉片煙的時候多,我父的卷子,早早因為詞意寬泛,被他斥落了。翁公本來想中我父,等到曉得錯誤了,急得眼淚望下直滴,孫公和其它的總裁考官,也個個都賠了嘆息。其實劉可毅並沒有到過高麗。後來袁公、沈公及翁公弢甫,都將這內中的詳情,告訴我父;外間也傳說都遍了。潘(按:潘祖蔭)、翁(按:翁同龢)二公愛重我父的才名,識拔我父的懇摯,可算得以國士相待的知己了。這幾位名公鉅卿,對我父的情義,直到現在我們後人,還是刻刻感念不忘的!」
對於這次的落榜,張謇極度傷感。在四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會試四次,合戊辰以後,計凡大小試百四十九日在場屋之中矣。前己丑既不中於潘文勤師,而今之見放又直常熟師主試,可以悟命矣。」想到連一向十分賞識自己的翁同龢也沒有錄取他,(其實每次會試主考官潘、翁二人都想取張謇,誰知三次都弄巧成拙,誤把別人的卷子當成張謇的卷子,致使張謇連考三次不中。),應該可以「悟命」了,於是「乃盡摒試具」,心灰意懶,無意進取了。他在自訂年譜中亦云:「計余鄉試六度,會試四度,凡九十日;縣州考、歲科試、優行、考到、錄科等試,十餘度,幾三十日。綜凡四月,不可謂不久,年又四十矣,父母必憐之,其不可已乎?乃盡摒試具」。
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壽特設恩科會試,據《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記載:「那年我父已四十二歲了,祖父也年近八十,所以科名的念頭,已經漸漸淡薄下來。那時三伯父在江西,由知縣奉委做慶典隨員,於是寫信給祖父,要我父也藉此機會到京一趟,祖父就答應了。命我父再去應試一回。到了北京以後,考試應用的文具,還是向朋友借湊來;放榜的時候,也沒有去聽錄。」
據張謇自訂年譜,四月十二日會試放榜得「第六十名貢士」。四月十六日複試得第十名。(註四)四月二十一日殿試,讀卷大臣八人:張相國之萬、協揆麟書、李尚書鴻藻、翁尚書同龢、薛尚書允升、唐侍郎景崇、汪侍郎鳴鑾、侍郎志銳。(註五)按照殿試的習慣,八名讀卷大臣中,官職最高的是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萬,其次是協辦大學士麟書,禮部尚書、軍機大臣李鴻藻排名第三,戶部尚書翁同龢排在第四,禮部右侍郎志銳排在第八位。因此張之萬選中的將成為狀元,麟書選中的將成為榜眼,李鴻藻選中的將成為探花,而翁同龢選中的也只能是第四名傳臚……志銳選中的也只能是第八。
當時翁同龢看中的人是張謇的卷子,四月二十二日翁同龢的日記稱「文氣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四月二十三日日記云:「定前十卷,蘭翁、柳門、伯愚皆以余處一卷為最,惟南皮不謂然。已而仍定余處第一(註六);麟二(註七);張三(註八);志四(註九);李五;薛六;唐七;汪八;麟九;唐十。」也是翁同龢的門生的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云:「是科翁師傅得張季直卷,必欲置諸第一,張子青(註十)不許,幾欲忿爭,……」因為張之萬看中湖南名士尹銘綬,而此次讀卷八大臣,由他領銜,狀元應由他取中,他不肯讓出,正是他維護自己的權利之處,況且翁同龢是翰林後輩,在禮貌上應對前輩退讓。
但翁同龢一心想要張謇得狀元,於是便去找李鴻藻商量,想讓李鴻藻讓出探花名額,想以探花再加上自己手中的傳臚兩個名額來換取張之萬手中的狀元,但是李鴻藻說:「狀元我不爭,探花我也不讓」。於是翁同龢只得去遊說麟書,最後說動了麟書,又加上志銳的支持,才為張謇爭到了狀元,而張之萬心目中的狀元尹銘綬當了榜眼(第二名)。張之萬時已老邁,而翁同龢又當時得令,以帝師膺殊眷,之萬也不便與之直抗,只好讓步。

清代殿試,所有試卷都要彌封糊名,試卷有數百本之多,讀卷大臣們挑出十本最好的卷子,要進呈皇帝本人親自審閱,皇帝大都照辦,很少更動名次的。確定狀元人選,御筆批上「第一甲第一名」(俗稱「點狀元」)之後,才拆開糊名,填榜公佈。翁同龢四月二十四日日記云:「上御乾清宮西暖閣,臣等捧卷入。上諦觀第一名,問誰所取?張公以臣對。麟公以次拆封,一一奏名訖,又奏數語。臣以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甚喜。」日記中的「又奏數語」,並未言明。香港掌故家高伯雨的推論翁同龢對光緒說,向來殿試注重書法,不重文章,此卷寫作都極好,以之為元,允無愧色。而且該年又是慈禧太后六十萬壽,張謇會試中六十名貢士,適符慶典,可為恩科得人賀。(註十一)
皇上甚喜,隨後於乾清官門外宣召,張謇遂以一甲一名蟾宮折桂。四月二十二日於太和殿舉行隆重典禮,授張謇為翰林院修撰,賜六品朝冠。禮畢,翁同龢又親往張謇所宿會館祝賀。張謇歷經二十六年的拼搏,終於蟾宮折桂大魁天下,到達了科舉取仕制度的峰巔,時年四十二歲,可謂「暮登天子堂」!
張謇之得狀元,雖云以書法勝於榜眼尹銘綬及探花鄭沅,但冥冥中如有神助。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云:「殿試之制,新進士對策已畢,交收卷官封送閱卷八大臣閱之,收卷官由掌院學士點派,皆翰苑諸公也。光緒甲午所派收卷,有黃修撰思永。比張季直繳卷時,黃以舊識,迎而受之。張交卷出,黃展閱其卷,乃中有空白一字,殆挖補錯誤後忘填者。黃取懷中筆墨,為之補書,此收卷諸公例攜筆墨以備成全修改者,由來久矣。張卷又抬頭錯誤,『恩』字誤做單抬,黃復為於『恩』字上補一『聖』字。補後送翁叔平相國閱定,蓋知張為所極賞之門生也。以此張遂大魁天下。使此卷不遇黃君成全,則置三甲末矣。」
張謇的試卷有一個挖補後的空白處未填字,光這「失誤」有可能就與狀元絕緣;另外試卷書寫時,要低二字寫,空上二字留為抬頭之用,文內頌聖提到皇上之處,另行「雙抬」,就是要高過其他行列的字兩格,但張謇只用了單抬,還好收卷官黃思永都幫他補上了。種種限制,不得踰越,這事若在雍正、乾隆年間恐怕要治罪了,但在晚清就較鬆了,但仍與前程有關。若不是黃思永助他一臂之力,就是翁同龢要爭,也無可如何,狀元可能花落別家了。
翁同龢對張謇才名的愛重,識拔的懇摯,真可算得以國士相待的知己。他〈題謇荷鋤圖〉云:
平生張季子,忠孝本詩書。
每銖常憂國,無言亦起予。
雄才能斂抑,至計豈迂疎。
一水分南北,憐君獨荷鋤。
學者都樾認為翁、張兩人交誼三十年,「始於相互傾慕,繼而成為師生,終於成為同黨」,患難與共,至死不渝,不僅成為晚清士林的一段佳話,更關係到晚清政局的起落跌宕。戊戌政變後,翁同龢罷官回常熟,曾經大權在握的重臣成為朝廷的「罪臣」,內心的苦悶與壓抑可想而知,且因他兩袖清風,為官四十餘年並沒有多少積蓄,他的日子並不好過。
南通與常熟隔江相望,張謇時常親自過江看望老師或派人送物送信,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十分頻繁。光緒二十五年張謇在日記寫著:「八月初三日巳刻,謁松禪師(按:翁同龢),感慨時事,誦念聖皇,時時咽嗚,午正共飯,酉初初刻謁退,師與危坐三十三刻之久,口無複語,體無倦容,以是知福澤之大且遠也。小人禍君子,往往而福之,為君子者,正宜善承天意耳。」
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初張謇派宗姓僕人到常熟送信送物,翁同龢的日記中有「得張季直函。白面四袋,小米一袋,每袋五十斤。山藥一簍,苡仁一包,白布二匹,花布二匹,洋手巾四打,香稻一袋。」
光緒三十年五月,張謇乘舟往常熟,訪松禪老人病,在日記上又寫:「十七日辰刻抵常熟,詣南涇塘,見松禪於病榻,頗惓惓於舊恩,大臣固應爾,抑西人所謂特性也!(另有記問答語,從略)。」翁同龢並口授張謇為其擬好遺疏略云:「已革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奏:為天恩未報,臣病垂危,伏枕哀鳴,伏念負疾如臣,固己言無足取,不敢復有所陳,第隆恩未答,盛世長辭,感悚之餘,難安瞑目,所願勵精圖治,馴致富強,四海蒼生,詠歌聖徳,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又張謇日記:「二十五日三兄以余生日,置酒召朋舊飲於壽松堂,始見報載松禪以二十日夜無疾而終,去十八日之別二日耳,遂成千古永訣,追維風義,豈勝愴痛!」二十七日,張謇在日記書寫道:「寫瓶師自輓聯,並自寫輓瓶師聯:『公其如命何,可以為朱大興,並弗能比李文正;世不足論矣,豈真有黨錮傳,或者期之野獲編』」。
翁同龢身故後,張謇又去過常熟兩次,第一次去哭弔;第二次在一九二一年去省墓,有〈虞山謁松禪師墓〉詩云:
淹迴積歲心,一決向虞麓。
晨暾徹郭西,寒翠散岩壑。
夾道墳幾何,鴿峰注吾矚。
停輿入墓廬,空庭冷花竹。
亟趨墓前拜,眥楚淚頻蓄。
悽惶病榻語,萬古重丘嶽。
抵死保傅衷,都忘編管辱。
尊騶貢大義,凝欷手牢握。
寧知三日別,侍坐更不續。
期許更或忘,文字尚負託。
平生感遇處,一一繚心曲。
緬想立朝姿,松風凜猶謖。
九原石台前,隨武不可作。
張謇後來為紀念翁同龢,曾在南通之黃泥山上卓錫庵舊址旁邊起一小樓,名曰:虞樓。「松禪師之墓在焉,輒來登眺,以致慕思」。張謇題寫〈虞樓匾跋〉云「黃泥東嶺,南望虞山,勢若相對,虞之西白鴿峰下,則翁文恭之墓,與其被放還山後,墓廬在焉。辛酉一月過江,謁公之墓,陟虞巔,望通五山,煙霧中青蒼可辨,歸築斯樓,時一登眺,悲人海之波潮,感師門之風義,殆不知涕之何從也!名虞樓以永之,亦以示後之子孫。」師恩難忘,綿綿不絕!
註記:
(註一)都樾〈翁同龢致張謇文稿繫年考訂〉,《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期,2011年1月出版。
(註二)同註一。
(註三)按:試卷雖然彌封糊名,但是閱卷大臣們可以通過筆跡辨識作者,於是,每逢會試之前,考生們便紛紛私下預測哪些大臣可能出任閱卷大臣,事先拉關係、走門路,呈送文字以便辨認。
(註四)據闈中內幕稱:「禮部右侍郎志銳初定張謇為第十一名,後翁同龢改為第十名。」
(註五)根據翁同龢日記所列八人次序是:張之萬、麟書、翁同龢、李鴻藻、薛允升、志銳、汪鳴鑾、唐景崇。
(註六)指狀元,張謇。
(註七)指榜眼,尹銘綬。
(註八)指探花,鄭沅。
(註九)指傳臚,吳筠孫。
(註十)按:張之萬,字子青,直隸南皮人,張之洞從兄。
(註十一)根據張謇之孫融武寫信詢問其世伯沈燕先生,沈君的覆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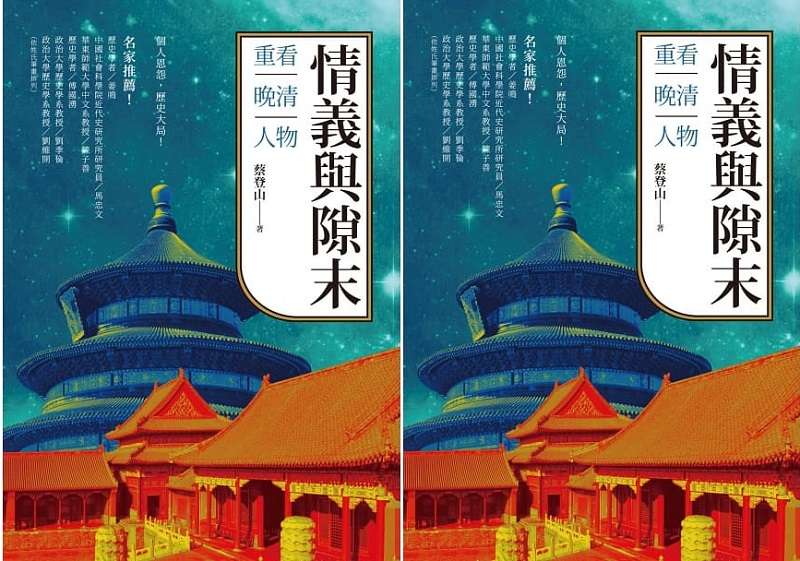
*作者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等數十本著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情義與隙末:重看晚清人物》(新銳文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