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中國興起了歷史熱。圖書市場上出現大量從各種視角重寫中國史的著作,既有國人的著作,也有譯著;既有傳統式的史學著述,也有跨學科的歷史研究,並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賣。
實際上,歷史熱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揆諸世界歷史,一個迅猛崛起的大國,其崛起本身會造成所處體系的深刻變遷,過去所習慣的參照系不再起作用,基於該參照系所設定的國家目標也會失效;於是,它無法再說清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麼、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往往會陷入一種深刻的身分焦慮。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沒有路標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在這個路口上,倘若它能夠在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與世界的內在一致性,就能夠將其龐大的力量轉化為對世界的建設性力量,並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歷史地位;否則,它將浪費自己所經受的苦難。為了真實地理解自己的處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處在十字路口的大國往往都會關注歷史,它們渴望通過對於歷史的重新理解,來廓清當下,構想未來。
這種身分焦慮的化解,無法簡單地通過對於某種價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自我身分,要基於兩種理論敘事的構建:一是政治哲學的敘事,它會為該政治體確立其所要追求的正義之目標;一是歷史哲學的敘事,它會確立該政治體的認同邊界,確認何者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兩種敘事加在一起,才會帶來政治體的精神凝聚力。單純依靠政治哲學的價值表述,無法回應共同體的特殊歷史處境;單純關注歷史的特殊性,則無法理解共同體與世界之間的內在一致性。當下中國的身分焦慮,實際上表達著對新的歷史哲學或者說新的歷史敘事的渴求;人們渴望通過對於中國各種特殊性的統合性敘述,來尋找中國通達於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對內對外的各種精神緊張。簡單來說,就是要在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上,回答「何謂中國」這一問題。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敘事,直觀上呈現為對過去的重述,實際上是在勾勒未來的方向;換言之,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是基於對過去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就是未來學。
要構建新的歷史敘事,首先需要有對於中國歷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於對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當中的結構性地位。那麼,中國歷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裡呢?
本書認為,它體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是一個軸心文明的載體,一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這兩點以一種人們經常意識不到的方式相互發生作用,幾乎中國歷史的所有運動邏輯,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所有切入點,都在對這兩點的把握裡面了。

所謂軸心文明,即在西元前八百年到西元前二百年之間的軸心時代出現的原生性文明。這個時候出現的中國文明,或許曾受到過其他文明的激發,並且在後續的年代中吸納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資源,但其內核中一些原生性的東西,作為基本識別要素,始終存在。軸心文明的特徵在於其普世主義取向,絕不自囿於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為思考單位;對應地,軸心文明不會設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擔綱,它所關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獲得普遍傳播。軸心文明的這一特徵,使得中國的精神結構中天然地有著普遍主義的衝動。在古代,它將自己理解為世界本身;在現代,它只有通過普遍主義才能理解自身與世界的關係,因為單純的民族主義理念無法提供足夠的精神容量,以支撐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軸心文明在歷史過程中都喪失了自己的政治載體,但東亞的軸心文明卻一直有中華帝國作為其政治載體,並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歷史效應。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中國的超大規模性。超大規模首先體現在中原地區的龐大人口與財富上,其規模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在第一個千禧年過後,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資源超過任何地方性勢力的抗拒能力,此後中國再無長時期的分裂現象出現,於是就有了國人經常說的「唯一歷史未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其延續性的根基並不僅僅在於其文明的韌性,更在於超大規模所帶來的軍事與財政邏輯。
說得更準確點,一個龐大政治體的自我維持,與軸心文明的存續,是兩個獨立的邏輯,並不能相互解釋,但是相互有需求。這個文明在其覆蓋區域內始終可以找到一個獨大強國作為其載體,該強國則始終可以該文明作為自己的身分識別標誌。而在其他文明區域內,由於沒有這種超大規模,沒有足夠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資源,因此能夠壓制各種地方性力量的獨大強國就很難持續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強國,便不會以文明作為自己的根本身分標誌,以免混同於其他國家。

中國軸心文明的擔綱者在古代的流轉,最終必會落在起自農—牧過渡地帶的人群身上,過渡地帶分布在長城沿線及東北。因為只有這個群體同時熟稔農耕與游牧兩種體系的秩序奧祕,能夠帶來超越於農—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長城南北的緊張關係轉化為統一帝國的內部均衡關係。他們對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夠調動中原的龐大財富,這是純粹的草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他們的草原身分使其擁有超越於中原的廣闊視野,有能力統治儒家文化無法直接整合的龐大非中原疆域,這是純粹的中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因此,這個群體能構建起龐大的多元複合帝國,使得軸心文明所構想的「天下」,外化為一個現實的帝國秩序。這種多元複合帝國也帶來中國的另一重超大規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規模性和帝國內部秩序上的超級複雜性。這兩個意義上的超大規模性,使得中國在現代轉型時面臨的任務變得極為複雜。
在擔綱者的流轉過程中,中國歷史經歷了複雜的變遷,變遷的主動要素,或說自變數,來源於社會分工最為複雜的中原地區。相對於非中原地區而言,因其分工的複雜性,內部各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係更為易變。每一次出現有歷史意義的技術躍遷,都會給中原帶來新的經濟資源,並打破此前諸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係,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會結構。舊有的和新出現的各種社會力量,會在動盪與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會結構就這樣經歷過幾次深刻變遷,從商、周之際的封建社會轉化為漢、唐之間的豪族社會,再到宋、清之間的古代平民社會。社會結構的變化,會改變中原地區的財政與軍事邏輯、帝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對力量關係、軸心文明的經典闡釋框架,以及中原地區與非中原地區的互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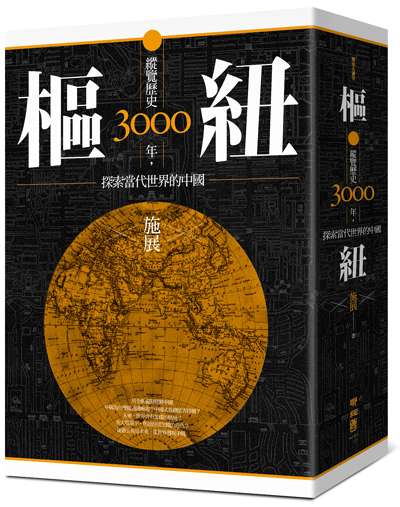
*作者施展為中國大陸知名青年歷史學者,曾發表專著《邁斯特政治哲學研究》,另有學術論文數十篇,時評文章數十篇散見於諸多刊物、媒體。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樞紐:縱覽歷史3000年,探索當代世界的中國》(聯經出版)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