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七十年,世界的先進社會就會喜不自勝地攬鏡自照,且對其所見沾沾自喜:成長。這面鏡子稱作國內生產毛額(GDP),而它已成為判斷我們有多美的主要標準,不管是從經濟和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都是如此。經濟──也就是GDP想衡量的東西──層層圍繞我們,你無法嗅聞它或觸摸它,但它是現代世界的背景噪音。它是新聞報導、商業頻道和政治辯論的主食。然而,對這麼基本的一個概念來說,出乎意料的是很少人正確地了解經濟是什麼,或我們如何衡量它的進步。我們只知道它必須持續不斷地向前進,像一隻鯊魚。
我們以GDP定義經濟。儘管GDP的發明人諄諄告誡,它已然變成國家福祉的代名詞。如果經濟正在成長,那代表情勢必然大好。如果經濟正在萎縮,那麼情勢可能不妙。然而我們一直以來顧盼的鏡子,其實是一面遊樂場凹凸鏡,而非浴室鏡,鏡子反射回來的影像受到嚴重扭曲,而且愈來愈和現實脫節。我們經濟的鏡子已經破裂。
我們生活在一個「憤怒年代」,它的定義是平民的反抗和拒絕過去珍視的體制和理念,這股趨勢可以回溯到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起。在美國,它促成川普(Donald Trump)的崛起。英國人已投票決定脫離歐盟,而在歐洲,右派和左派的非傳統政黨也已撼搖現狀。從印度到巴西以及從菲律賓的土耳其的平民反抗,無不引發政治震撼。

有許多不同的理論嘗試解釋,平民的憤怒為什麼發生在這些以主流方法衡量從未像今日這麼富裕過的國家,但這些理論有一個共通的線索,就是人們沒有看到他們的生活反映在官方的圖像中,而這個圖像主要是由經濟學家所描繪。這股反抗的勢力有一部分源自認同的問題、無助感、缺少負擔得起的住房、社區的式微,以及對金權政治和不平等升高的憤怒。本書的目的在於解釋專家對我們生活的說法,和我們對生活實際的感覺之間的鴻溝。
雖然幾乎所有人都聽過GDP,卻很少人知道它是直到一九三○年代才發明的工具,先是用來因應大蕭條,然後經過修訂用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作準備。我們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是,經濟不是一個自然現象,它不是等著發現的真理。在一九三○年以前它實際上不存在,它是人創造的東西,像棉花糖或汽車保險,或是複式簿記。
如果GDP是一個人,它對道德將不會有感覺,甚至會視而不見。它衡量各種各類的生產,不管好壞。GDP喜歡汙染,特別是你必須花錢清除的汙染。它喜歡犯罪,因為它喜歡龐大的警力和修理被打破的窗戶。GDP喜歡卡翠娜颶風,而且對戰爭沒有意見。它喜歡計算為衝突而整備槍砲、飛機和飛彈,然後它喜歡計算城市遭戰火蹂躪成殘垣斷瓦後的重建成本。GDP很精於計算,但對判斷品質卻不在行。它完全忽視餐桌禮儀。對GDP來說,三把叉子的晚餐餐具擺設只是多餘,它只需要刀、叉和湯匙。
GDP是傭兵。它不計算沒有金錢換手的交易。它不喜歡做家事(至少我找到一個共通點),而且它逃避所有志工活動。在貧窮國家,它對如何計算大多數人的活動傷透腦筋,因為這些活動大部分發生在金錢計算的經濟之外。它可以計算超級市場的一瓶礦泉水,但無法計算一名衣索比亞女孩步行好幾哩路到水井汲水對經濟的影響。
成長是一個達到生產年齡的兒童,而GDP的設計主要是用來衡量體力的生產。它難以分辨現代的服務經濟,對像保險和花園造景等服務業占主要部分的富裕國家來說,這是個明顯的缺點。它對計算磚頭、鋼筋和腳踏車的生產──「你可以拿來砸自己腳的東西」──很管用;但試試用它來計算理髮、心理分析時段或音樂下載,它會明顯地變得力不從心。它對衡量進步並不靈光,但這卻是我們以為它靈光的項目。就我們衡量成長的主要方法而言,一顆抗生素只值幾美分,雖然在一百年前一個染患梅毒的億萬富豪可能願意用一半的財富交換一個七天的療程。
總之,我們對經濟的定義相當粗糙。就好像有人半開玩笑對作者說:「如果你陷在交通阻塞一個小時,這對GDP也有貢獻。如果你到朋友家裡幫忙做點事,那就沒有貢獻。」他說,反正「你只需要知道這一點就夠了」。如果你懷疑這個人說錯了,我希望你繼續讀下去。
我們都直覺地認為這個解釋不對勁,卻又不知從何說起。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極其明確的訊號,說明經濟學辜負了我們的期望。在之前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和接踵而來幾乎整個西方世界陷入衰退時,成長的狂熱教派曾帶領我們讚頌我們的經濟。像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這些人說,情勢一片大好,我們應該放任市場創造愈來愈多財富。

事實上,我們的標準衡量方法並沒有告訴我們成長是怎麼創造的:實際上成長是建立在快速膨脹的家庭債務基礎上,而這種債務則是由狂熱追求紅利的銀行家用愈來愈巧妙(或愈來愈愚蠢)的金融設計所創造的。先進經濟體原本應該已達成被稱為大穩定(Great Moderation)的新天堂,在這個理想世界中,聰明的技術官僚已讓經濟榮枯的循環成為歷史,市場只要任由它自己發展就一定能達成皆大歡喜的穩定狀態。
經濟成長並沒有告訴我們不平等正在升高,也不讓我們了解全球失衡的嚴重性。美國的貿易逆差正不斷膨脹,支應這種逆差的是中東產油國家和中國,而這些國家則把貿易順差轉換成美國公債。中國實際上是在借錢給美國人,以便美國人買得起在世界工廠製造的所有東西。這正是讓成長的旋轉木馬得以持續旋轉--直到它停止--的原因。多年之後,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仍然無法回到二○○八年以前的水準,特別是部分歐洲國家。它們赫然發現,多年之前的成長有許多是幻象。
成長的問題之一是,它需要無盡的生產,以及它的表親無盡的消費。除非我們想要愈來愈多的東西和愈來愈多付費的體驗,成長終究會減緩。要讓我們的經濟持續向前進,我們必須有永遠無法滿足的胃口。現代經濟學的基礎是,我們對東西的渴望是無限的。然而在我們內心深處,我們知道這條道路的結果是瘋狂。
幾年前,諷刺雜誌《洋蔥》(Onion)刊登一篇有關陳賢(Chen Hsien)的文章,他是一個虛構的中國工人,為無聊的美國人製造虛構的「塑膠大便」。這篇典型《洋蔥》式文章的諷刺幾近侮辱,卻一針見血道出問題所在。陳賢不斷搖頭,不可置信地說他被要求製造的廢物包括從沙拉切削機、塑膠袋分配器、微波煎蛋捲機、會發光的閱讀放大器、耶誕節主題的檔案籃、動物形狀的隱形眼鏡盒,和自黏式牆勾等。「我還聽說,當人們不再需要一種商品時,他們就直接丟棄。這麼浪費,一點也不懂得愛惜。」他輕蔑地說。「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廚房用具?」陳賢困惑地問。「我可以了解要有好炒菜鍋、煮飯鍋、水壺、烤盤、一些用具、好瓷器、裡面有過濾網的茶壺,也許還有溫度計。但所有這些多出來的東西──美國人要放哪裡?你會用玉米餅皮盤多少次?『噢,我真的需要這種銀器抽屜整理盒,否則我會瘋掉。』閉嘴,蠢美國人。」
陳賢的抱怨挑動我們的神經,因為在富裕國家大多數人知道我們不斷購買東西,儘管是我們知道不需要而且絕不會用第二次的東西。廣告加上朋友和鄰居的欽羡,促使我們買更多和不斷更新。等到你讀本書時,我的iPhone 5將已成為古董。我們也知道像洗衣機和烤麵包機等產品的設計都刻意讓它們很容易壞,以便我們在一個永不停止的消費循環中會繼續購買。
陳賢製造的東西聽起來很荒謬,但它們絕不是虛構的東西。天空商場(Skymall)的購物目錄讓航空旅客可以舒服地在座位上訂購各種非買不可的商品,包括一幅你的寵物穿得像十七世紀貴族的畫像(四十九美元),可懸掛的松鼠頭(二四‧九五美元)、實物大小的懸掛叢林猴塑像(一百二十九美元),以及最重要的,狗狗專用的橡皮唇(二九‧九五美元)。當經濟學家說當今世界的問題是長期缺少需求造成的時,我們實在搞不清楚我們還需要什麼。
從經濟學的觀點看,世界從來沒有這麼美好過,我們的消費力從來沒有這麼強大過。美國從一九四二年首度公布國民帳(national accounts)以來,一直以近乎快馬加鞭的速度成長。英國和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情況也類似。二○○八年金融崩潰的挫敗後,大多數經濟體迄今已重回成長的軌道,雖然速度略微減緩。因此即使成長的力道減弱,我們經濟體的規模也從未如此大過。如果累積的成長能夠代表福祉,那麼我們肯定從沒有像現在這麼滿足過。
把太多信心寄託在成長上有一個明顯的問題,那就是它的成果從來沒有被平均地分享過。我們的平均所得--或福祉--的標準計算方法是把國家的經濟大小,除以居住在這個國家的人數。平均是一個陷阱,能造成嚴重的誤導。銀行家賺的錢比麵包師傅多,麵包師傅賺的錢又比失業者多。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如果一個富裕國家的整個經濟大餅都由一個人獨享,其他人都吃不到一口,那麼平均來看每個人應該可以過得不錯,太好了。但實際上許多人會餓死。
真實世界不會那麼極端──可能除了北韓以外──但即使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平均也可能相當傾斜。讓我們想像一下每年創造的財富有一大部分都流向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口。聽起來不太可能嗎?事實上,頂層○‧○一%的美國人,相當於一萬六千個家庭,他們從一九八○年至今分享的全國財富增長為四倍。他們吃到的美國經濟大餅比率,比起他們的同階層在十九世紀末所謂鍍金時代(Gilded Age)吃到的還大。如果你的國家經濟成長唯一的原因是富人變得愈來愈富,而你卻必須工作得愈來愈辛苦才能維持生活水準,那麼你有權利問:所有這些成長的目的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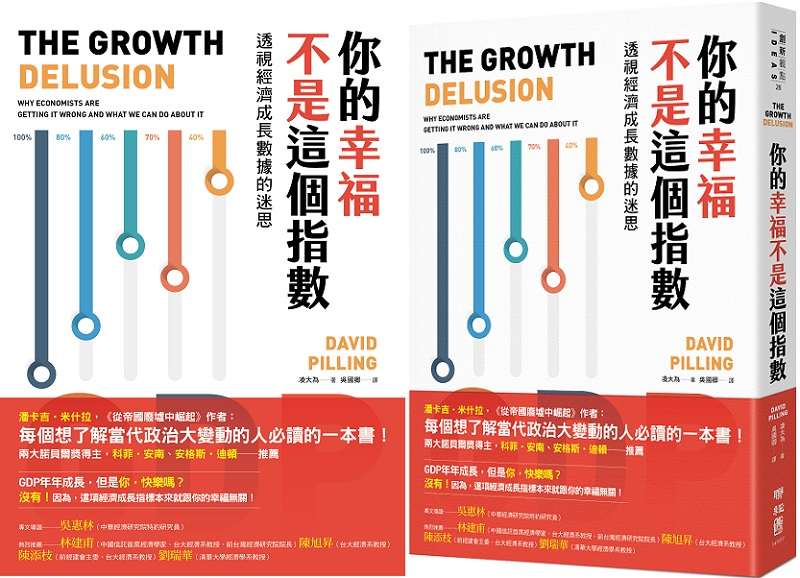
*作者凌大為(David Pilling),《金融時報》非洲版主編暨專欄作家,曾任亞洲版主編,2002至2008年擔任駐東京辦公室主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透視經濟成長數據的迷思》(聯經出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