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浙江蕭山縣寒士鍾俊連捷登第之後,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在同年宴上結識了御前侍衛山西人白某。白氏家境素豐,有女及笄,想贅一個風流俊賞的讀書人為婿,好改換門庭。鍾俊是個素心人,讀書就是為了消閒,原本沒有做官的巴望,也沒有什麼振家聲、顯父母、耀門楣的大志,考得了功名,想是起碼過幾年安穩日子,不料有人來給說合,結親就結親,隨緣無不可。
南陽府地屬河南,實亦轄湖北襄陽,是個大鎮。從京城到南陽,走水路雖然繞遠,但是行程最為便捷,雲帆高舉,不數日即至維揚,再換船溯江西行,也只有幾天的航程就能抵達。但是舟行也有麻煩的地方,啟程泊岸之際,上下行李,比之騾馬馱橐,要費事得多。尤其是白家老丈人,身為廷衛,久居宮禁,結交的達官貴人不少,新婚饋贈所得自然非比尋常。加之以自家備辦的妝奩,其豐厚可知。於白侍衛而言,送女婿登程履新,應該算是一大盛事,所以刻意鄭重其事,光是陪嫁的丫鬟奴僕,就有百人之眾,雇來扈從運送的船隻,竟多達數十艘。啟航從京師至通州四十餘里,連路旁看熱鬧的都絡繹不絕於途,沿河逐走,看了一天一夜,人潮才漸漸散去。
這一頓排場,在白侍衛而言,不誇誇然熱鬧一回,還真怕江湖中人不知道是他老人家的閨女要出閣呢。換言之,正是這麼敞開來炫耀,倒帶著些許諸葛亮撩撥司馬懿的意思,彷彿是說:哪個有膽不要命的綠林宵小敢做這一趟打劫的買賣,就不要怨我白某人事先沒打上招呼。
可白侍衛不曾料到,宮門長鎖,衙門長開,大內之中上下百多年,打轉的不過是一家人;可官場之上也好,江湖之中也罷,風水人事畢竟是活絡的,誰不會說幾句「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彼何人也,予何人也」這一類的話。說這話是個什麼意思呢,不外就意味著後起之秀未必能明白、也未必肯敬重老輩兒人的身分;換言之,總有那麼些不曉事、不通情、不知分寸的人物,還是看上了鍾俊他小兩口兒的一大綱家私。
有心幹它一大票的不知道白侍衛名震京衛,也不計較船上有些什麼人,只知這船隊沿途停靠的俱是通都大邑,等閒不好下手。而船行卻越走越慢,彷彿雇主並不自覺已經身在覬覦者的眼下掌中,仍自好整以暇,貪玩風月。
這一天舟抵維揚,要從運河換入江行,不但得改為西航,有一部分貨運還得換船。鍾俊和年輕的妻子白安人為了騰出艙中的空兒來讓家僕出入,索性在船首架了個矮几子,小兩口兒對起棋局來。落子之初不過是申正時分,到中局,天色已經向晚了,白安人下得興起,不肯離船,鍾俊也覺得港口一片熱鬧,吵擾得很,小夫妻倆一合計,說是乾脆溯江而上、繼續趕路的好,畢竟維揚是個大地方,再走個幾十里路,未必沒有小一些也靜悄一些的港汊津渡,自凡能泊舟過夜,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奴僕們傳喚船家啟航的話一嚷嚷開來,尾隨而至的船匪們可就樂了,他們知道,無論今夜在何處停泊,這一支船隊都逃不出他們的手掌心兒了。眼前他們能做的,就是趕忙聯繫附近水滸之中能通上聲氣的同行,收拾更多的載運船隻,於一戰得手之後,立刻搬運贓物,鑿沉原舟,而不驚動十餘里之外維揚港口的官兵。
地頭上也的確是另有幾撥兒水盜,各擁一、二舴艋小舟,但是合起夥來,共奉一名水性極好的江湖大哥為首。此人姓王,單名一個凌字,外號鎮江王;顧名思義,其勢力之大,可以溯流而上,直達鎮江。不過,另有一個說法,說他能夠溯江上泅,一鼓作氣,由維揚直達江寧,這樣的本事,就算是當年梁山泊的「浪裡白條張順」都不能及,可謂能夠「威鎮長江」了。所以「鎮江.王凌」才算是他真正的諢名兒。
「鎮江王王凌」也好、「鎮江王凌」也罷,總之一聽有這等好買賣,哪裡還肯放過?登時催發了百數十艇快船,呼嘯而至。船家們眼尖,遠遠聽見打呼哨,再看火炬分而復合、和而復分,這是水面上的買賣家慣玩兒的把戲──也算是一門絕活兒了──將火炬隔舟拋遞,往來不停,遠遠望著,在一片黑暗之中只見鬼火飛跳,此起彼落,倏忽明滅,聲勢十分駭人。船家水手看不多會兒,紛紛喊叫起來:「是『鎮江王』的勢頭!是『鎮江王』的勢頭!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鬧亂是幾數息的工夫就傳遍各大小船艘的,奴僕們將水手的言語跟鍾俊一叨咕,嚇得這書呆子登時觳觫不已。就在這時,卻聽一旁的白安人開口道:「小丑何敢跳梁?」
一句話說完,回身朝一個貼身的丫鬟使了個眼色,但見那丫鬟向空一甩雙臂,作了個揖,外罩的長裙已經在轉瞬間脫了去,半空中卻爆起了個不大不小的煙火。接著發生的事讓鍾俊驚訝不已:一霎時間,各船船頭都站出來個丫鬟,人人短打衣靠,黑衫黑褲,望之猶如一片黑墨,這些個黑衣丫鬟似乎是不約而同、或者是早就操練過了似的,分別囑咐船家水手,立刻將各船船身用鐵鎖串連成一氣,打熄了燈火,合拱著鍾俊所在的官船居中。
片刻之後,眾丫鬟已經排成了一列隊伍,一個兒輪一個兒來到矮几之前,由白安人發給一握棋子,吩咐說:「不過是些個蝥賊,萬萬不興許放他們登上船來,要是驚嚇了官人,我唯你們是問!」
丫鬟們銜命而去,白安人這也才好整以暇地甩開自己身上的連身長裙,露出了裡頭的黑羅衫褲,青布蒙頭,不知從什麼所在摸出一囊沉甸甸的鐵丸,掛在腰間。鍾俊看她神色是眉立目揚,英武神俊之態,一點兒也不像新嫁以來的模樣,不由得期期艾艾地問:「你、你、你要上哪兒去?」
白安人嫣然一笑,道:「不就是防賊去麼?你要是不害怕,隨我來,瞧瞧。」說著,拉起鍾俊的手,相偕躡步藏在艙門裡側。
此時「鎮江王」的盜船也已經一字排開,與官船居中的這幾十艘貨船隔著不到一箭之遙的江面,緩緩靠了過來。這是個陣頭,此時的貨船要是不至於驚惶四散,盜船便仗著船多,乘隙圍攏,待把貨船像驅鴨趕鵝似地侷促到團團一隅之地,不消半晌工夫,便可以登艙擄掠了。
說到這兒,就得岔嘴說一說白安人的布陣之道了。這一番防賊禦盜,當然不外是行前白侍衛的一套交代:平日習武不輟的這幾十個丫鬟們,人人駐守一船,外服長裙、內著短靠,遇事先將船隻鎖了,免得臨陣讓人驅趕成聚食之蟻的一般。
至於為什麼鎖上船、而不怕船盜用火攻呢?道理很簡單,一旦要放火,必然是飽掠金珠財物之後;換言之,必然是賊夥登船行劫、事畢之後。倘或一對陣就放火,船船鐵鎖相連,當然難以收拾,那麼放火的盜賊反而一無所得,白忙一場。這是為什麼白安人仔細叮囑「萬萬不興許放他們登上船來」的道理,因為一旦讓船盜登舟,那些熟練的強人還真會在得手之後放一把火,那可就萬劫不復了。
這且回過頭,說「鎮江王」這一頭。「鎮江王」在這長江中下游一帶討生計,也不只三年五載了,仗著自己水性高人一等,聚成大夥,都說是當年橫行大宋朝十數年的洞庭湖楊么托生的水中丈夫,數百載以下無與倫比者,可連這首領王凌也沒見識過:居然有這麼一支既不似官櫓、又不似戰艦的船隊,能夠擺出這麼個陣式來,而且諸船一字橫江之後,竟熄燈偃息,不見一絲一毫的動靜,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懷疑未決之際,片刻如經時,等盜船逐漸逼近,雙方船頭之間不過是丈許寬而已了,王凌左顧右盼,看這排面拉得太寬,怕號令不及,萬一有個平素往來疏遠的水滸弟兄一時認不清號令,或者是著慌放了火,船鎖連綿,把這筆大好的買賣付之一炬,豈不可惜可憾?於是匆促之間,急飭所屬:趕緊滅了火把,持撓鉤利刃登船,一探究竟。
接下來的事,就更出人意料之外了。王凌一聲號令才傳下,有那早就盯梢許久、知道船上有眾多女眷的水賊,根本不屑得取兵刃,赤手空拳便搶著往這邊船頭蹦跳,可說也奇怪,不過幾尺寬的水面,卻沒有一個跳得過的,頭一撥兒或是發狂吶喊、或是嘻笑喧騰的水賊便像餃子落進湯鍋裡的一般,全下了水;更令王凌不解的是:這些平日水性精熟的餃子們一下水就彷彿沉了底,一個都浮不上來了。
饒是王凌耳聰目明,看見這些個嘍囉們縱身半空之中的瞬間,似有尷尬物事,像暗器一般,來得迅猛凶險,於是搶忙呼喊:「退退退!」說時已遲,那時已至,喊退卻還來不及退的節骨眼兒上,又給暗器打落了十幾個。
王凌一則以驚,一則以怒,想:此時不殺向前去立威,我「鎮江王」這一塊招牌豈不立馬就砸了?轉念到此,順手抄起原先立在船頭防箭的大鐵盾,握著5尺板刀,猛提一口真氣,飛身朝當央那條看來大了許多的官船撲躍過去。人還在半天裡,就聽得鐵盾之上叮叮咚咚雨點冰雹也似地砸落了不知多少物事,待他雙膝蜷定,兩腳落實,人在甲板上一寸一寸向前挪移的時候,不料鐵盾底下一時留了個縫兒,教飛進一枚鐵丸兒來,正擊中了大拇趾。手指足趾連心,疼痛自是難忍,王凌一低頭,鐵盾歪開,頂上又捱了一枚鐵丸,這一下他可釘不住了,仰面翻倒──練家子畢竟還是練家子──就在這匆匆一跌之際,他瞥見了官船艙門口的女子:青巾覆額,黑衫黑褲,眉目姣好,玲玲瓏瓏的纖腰上掛著一囊讓他栽盡跟頭的鐵丸。
「鎮江王」一落水,眾船盜再也無心戀棧,紛紛呼喊:「大王下水啦!大王下水啦!」語畢,投江而遁,連船都不要了。
局勢逆轉,也就是頃刻間事,白安人當即做了處置:讓眾船一齊舉火,照耀江面,如同白晝,看看有沒有倖免於滅頂的盜匪,搭救上船,用麻繩索子縛了,準備第2天派人解回維揚去。
鍾俊開了眼界,恭謹之色溢於言表:「夫人究竟有何神術?治大盜竟如同約束小兒一般,果然是將門的豪傑,看來是所向無敵、所向無敵;佩服!佩服!」
「說無敵就忒誇了,實則也沒什麼。」白安人雲淡風輕地說:「父親喜歡騎射,家中庭院,總是整治得比較寬敞。
「我小時候窗外有長牆一堵,牆裡的小徑又直又長,父親將就地勢,以之作為箭道。我沒旁的可玩兒,便拾些石子兒扔那箭道上的靶子。父親看我扔靶子扔得有興致,定了賞格,我練得就更起勁兒了。非但自己樂之不疲,還夥著身邊的丫鬟們一塊兒練,不過2、3年之間,人人都能夠百發百中了。
「這還不算,父親又用人形做靶,周身畫上穴道,倒也不算難,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便不失手了;最後再用牛革製靶,練鐵丸投射之技,4、5年下來,所擊無不洞穿。
「倒是父親還常開玩笑說:『這娃兒可已經稱得上是天下無敵女將軍了!』不過,練得一班老小丫鬟們能認穴、打穴罷了,所擊之穴不失分寸,的確可以傷人,可稱不上什麼無敵就是。」
「只不過棋子是個小玩意兒,能傷人也的確是神奇。」
「方法用熟,粒米可以殺人,何況是棋子呢?」
「還有一樁不明白,」鍾俊道:「這些個丫鬟們領了棋子,各回己船,怎麼不見她們出來應戰,卻已經克敵致果了呢?」「這倒是預先就想妥了的。」白安人笑道:「我料江中必有賊盜,才讓丫鬟們早早穿了黑布短靠,猱踞於桅杆之上,由上往下俯視,非但目力明,且用力遠,衣色恰在夜色與杆色之間,闃暗朦朧,賊盜亦無從察覺。」
「你自己卻匍匐於艙下,這又是什麼道理?」鍾俊還真是打破沙鍋──璺到底!
「賊首一見嘍囉們不能取功,就想要一舉擒殺吾等主帥;主帥究竟置身何處呢?在他們看來,必然是中央這一艘大官船。即便他猜中了,也必然以為我們也躲藏在桅杆之上,顧了高處不能顧低處,就不免下盤露空,予我以可乘之機了。」
鍾俊聽白安人侃侃道來,略無半點驕矜之色,自然是益發欽敬了。
閒話不多提,且說鍾俊赴任之後,倏忽六載,任滿之後,調首邑,先署理布政使司,算是權掌河南一省政務,地位僅在巡撫之下。
在之前這擔任南都之宰的6年裡,他最主要的功績也是軍功,不過這些個軍功倒不是白安人給立下的,主要的是──前書說過鍾俊還真是打破沙鍋璺到底!──南陽府也兼領著襄陽地區的防務,在這段期間,地方上不是沒有水旱綠林之輩想要乘勢鬧祟,卻總是能敉平於未發之際。
起初鍾俊也同一般的官吏一樣,還倒是官運亨通,諸事大吉,不料自己這麼個不忮不求的為官之道,還真獲得了老天爺的憐寵、庇佑。久而久之,同湖廣總督和河南巡撫這一班封疆大吏接觸得多了,才間接得知:能夠敉平地方上的匪類,清剿盜藪,並不是倚仗自己洪福齊天,而是介乎河南、湖北兩省之間,有一支隸屬於湖廣總督轄下的游擊部隊,數年來偵伺、潛伏,時時掌握盜賊行蹤動向,往往制敵以機先,防患於未然;而那部隊長銜加游擊,姓許,單名一個傑字,正因為直屬湖廣制台調度、節制,所以鍾俊幾乎不知道還有這麼一號人物。
倒是有一回豫、鄂督撫會食,鍾俊才得以同許傑見了面,鍾俊見這許傑身形魁梧,膀闊腰圓,星目隆準,大耳虯髯,的是一流的英雄人物,自然歆羡歡喜,一攀談,發現此人慷慨豪邁,果真不負他堂堂儀表,心下更是崇敬有加,刻意要深相結納。
知府卸任前夕,是大暑天氣,京師裡傳言蠭出,都說鍾俊署理河南布政使的時日不會太長,說不定一到任就真除了,畢竟是娶了個好媳婦兒,朝中有梁木撐持,際遇自是不同。謠諑紛紜,夤緣交際、趨走攀附的更不在少數,由於天氣實在炎熱,送往迎來本已不勝其擾,而鍾俊又十分不耐應酬閒話,正準備閉門謝客,門上投了拜帖來,打開一看,是游擊許傑。
許傑來謁,應該不是虛與委蛇、拍馬捧場來的,他開門見山遞上來一卷輿圖,鍾俊展卷一看,大為訝然:原來這是一軸手繪的運河輿圖,自凡是京師以南、經通州而揚州,子午一線,所經之地水滸形勢、盜匪盤據情況,無不隨圖附注,巨細靡遺。
許傑的話說得也簡明扼要:「某與大府相見恨晚,然而看大府神色不凡,逸出群僚之上,是孜孜矻矻、戮力於民事之慈悲長者,乃肯以此卷相贈。
「大府若是署理河南政務,但請持此圖一一尋訪,與各地盜藪約說,請無害於商民。江湖賊盜之屬,鋌而走險,往往迫於無奈;但須有長者扶持導教,開拓生理,往往令至而晏然。大府持圖而去,又能說之以情,而不加之以兵,他們自然也會畏懼、感念,一旦方面有警,不定還會是莫大的助力。」
對於即將履新的鍾俊而言,這一份輿圖大禮不只是捕盜用兵的諜報,也是撫庶輯民的指引,一番愉悅之情,自清涼無汗;回頭見許傑頭頂上還戴著頂笠子狀的官帽,端的是汗出如漿,鍾俊隨即吩咐小廝:給許游擊打來熱手巾把兒,順便捧了帽子去,好涼快涼快。孰料許傑連忙搖手,道:「不必!不必!」
鍾俊怪道:「這麼熱的天,咱們又是便中清談,怎地還戴著帽子呢?」
許傑想了想,道:「實實不敢相瞞於大府──我原先是長江裡的巨盜,以『鎮江王凌』聞名,因為擅劫官船,不慎失手,非但葬送了百數十名兄弟,瓦解幾十處水滸,自己也受了傷,額頭頂門之間捱了一粒鐵丸,削去頭骨一塊,幸虧後首以『兒腦丹』治癒,可卻不能經風,是以無論多麼炎熱的天氣,都不敢除帽。」
鍾俊聽到這兒,略有所覺,遂接著問道:「老兄勇冠三軍,在襄陽一鎮立下戰功無數,敉平盜匪數以萬計,怎麼會受這麼重的傷呢?」
許傑歎了口氣,苦笑道:「說起來,這傷了我的女子,還真是我的恩人呢!她那一鐵丸打在我頂門上,我才看清楚:傷了我的居然是個姑娘家──大府試想:一個女流之輩隨手便能夠把我『鎮江王』打翻在水裡,幾至於溺斃;我,還能闖蕩出個什麼天地來呢?可是空有一身筋骨膂力,別的事也貪圖不得,不如投軍,立幾級『首功』,倒還順理成章。能夠忝然混到今日,當得一員游擊,豈不都是恩人那一鐵丸所玉成的呢?」
「那麼之後老兄見過你那恩人沒有?」
「落水之際,匆匆一瞥,之後再也不曾見過。」
「想不想見見你那恩人呢?」鍾俊笑著問道。
「天涯海角,如何見得?」許傑搖了搖頭。
「來呀!」鍾俊跟那送手巾把兒的小廝吩咐了一聲:「有請白安人。」
俠女和大盜不打不相識,因殺機而獲生機,化仇作恩,竟爾別後重逢的故事在此作結是恰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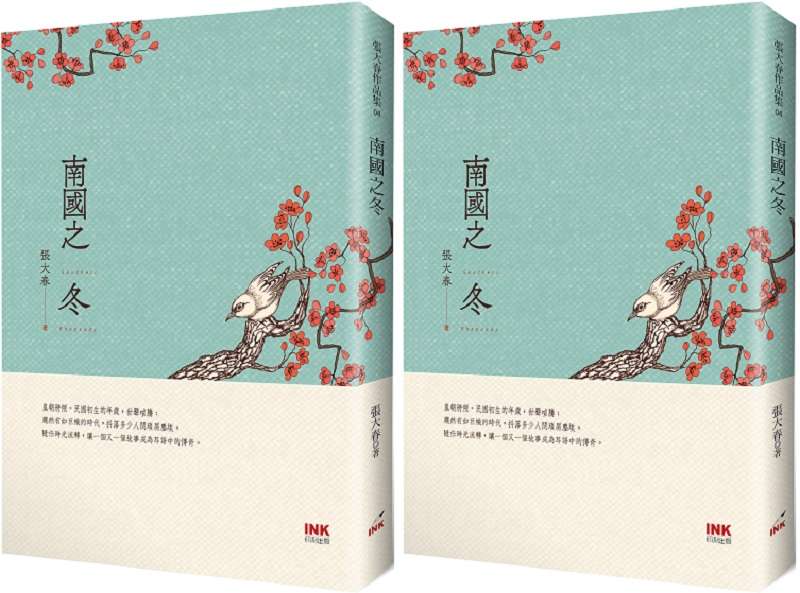
*作者為知名作家,現任電台主持人。曾獲聯合報小說獎、時報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小說《南國之冬》(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