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多數東歐人都將烏克蘭視為一個與世隔絕的神祕國度。當年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Karl XII)去烏克蘭結交盟友共同對抗俄羅斯時,他坦承「不確定該走哪條路」;六十年後,英國旅遊作家約瑟夫.馬歇爾(Joseph Marshall)在一七六九年也遇到相同困擾:「烏克蘭是如此偏僻,近一百年來都沒有人去過,沒聽過任何人與世界分享自己的觀察心得。」將近兩百五十年後,這個國家對多數歐洲遊客而言依然是個謎。
話說回來,美國對烏克蘭而言也是個謎。我下山後搭便車到拉克赫夫(Rakhiv),再轉搭巴士去烏日霍羅德(Uzhorod)。途中,一位名叫露德米拉(Ljudmila)的女大學生在胡斯特(Khust)上車,坐在我旁邊。她說自己經常夢想住在美國,對二次大戰歷史很著迷,於是我就測試她:「你知道蘇聯和美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是盟友嗎?」
她錯愕地看著我,「真的?」
「你聽過雅爾達會議嗎?」
「什麼意思?雅爾達發生過什麼事?」
我解釋:「邱吉爾、羅斯福和史達林曾在那邊討論戰後要如何分割歐洲,他們最後同意將西歐歸由英國和美國管理,讓俄羅斯管理東歐。」
她看起來很疑惑。「你有沒有聽過D日?」我發覺烏克蘭人可能會用另一個詞稱呼它,所以我又補充:「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有沒有印象?」
「沒有。」
「那天有三萬艘戰艦和十七萬名盟軍橫越英吉利海峽,進入歐陸。後續的幾個月內,數百萬名美軍將戰線推進到德國。」
「我從來都不知道大戰期間有那麼多美國人在歐洲。」她承認。她以為蘇聯是納粹敗戰的唯一原因,其他同盟國都沒扮演任何角色。
我告訴她:「我猜你們的學校也沒教過北非和日本附近的戰事。」
她開始惱怒了,「我不了解學校為何沒有教更多,我們的教授看起來滿客觀的,也很有知識,他是反共產主義的。我們的歷史書籍也是新的,不是共產時代的舊教材。」
雖然重寫歷史只需要一天時間,新觀念卻可能要等一個世代才能滲透整個社會。當時烏克蘭已經獨立了二十年,但這位二十歲的高材生對於二次大戰的一些基本常識依然一無所知。不過話說回來,一位二十歲的美國人也不見得能在世界地圖上指出歐洲。
無知也可以在鄰居之間交互傳染。尼爾.米契爾教授告訴我:「我最近要去波蘭授課,地點距離烏克蘭的邊界不到一百公里。我原本想順道去一趟烏克蘭,於是就向波蘭的聯絡人詢問了一些相關細節,她似乎以為我要去中國!她很訝異有人會想從波蘭拜訪烏克蘭。」
巴士搖晃著經過胡斯特、別列戈沃(Berehove)、穆卡切沃(Mukacheve),最後終於抵達烏日霍羅德,一個位於斯洛伐克邊界的優美城市。烏日河(Uzh)將它分為舊城與新城。我在等待前往斯洛伐克的夜車時遇到一對俊男美女米洛許(Milosh)和坦雅(Tanya),他們主動邀請我搭便車快速參觀舊城區。我們開車上了山丘,上面有一座維護完善的十六世紀城堡,我們走到民間建築與生活博物館,它沒開門,但米洛許賄賂警衛讓我們進去。他說:「烏克蘭人就是吃這套。」逛完露天博物館,了解烏克蘭人的古代生活後,我們繼續逛舊城區。我們經過了一間預計下個月會營業的冰淇淋店,價目表還沒貼出來,但它們會比義大利賣得便宜。烏克蘭在當年(二○一○年)擁有全球最便宜的大麥克(一點八四美元),挪威則是最貴的─貴到爆炸的七點二元。米洛許和坦雅從未嘗過義大利冰淇淋,我給了米洛許一些現鈔,交代他屆時一定要好好招待坦雅。他們笑著祝福我之後旅途順利。
烏克蘭的未來
烏克蘭的國歌標題是Sche ne vmerla Ukraina(烏克蘭仍在人間),第一句的意思是「烏克蘭的榮耀尚未逝去」。這讓我想起波蘭國歌,它基本上也是在說「我們還沒死」,這兩個國家似乎在潛意識中都知道自己總有一天會再度被迫就範,他們似乎永遠懸浮在動盪邊緣,只要強大的鄰國打個噴嚏,他們的世界隨時就有可能變色。果不其然,普丁爆出了一坨黏稠的鼻涕。

我問瑞克對烏克蘭的未來有何看法,他回答:「烏克蘭數百年來都停滯在邊緣狀態,我預期這種情況會持續,而且這不盡然是壞事。這取決於它的地理位置,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雙重文化特質。我覺得它一直都會在歐盟和俄羅斯之間拉鋸,或許十年後的歐盟也不會再那麼誘人,天曉得?烏克蘭已經當了數世紀的搖擺人,它不太可能會在此刻做出明確的抉擇。」
烏克蘭至今仍無法擺脫進三退二的迴圈,但瑞克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不會走上共產主義的回頭路,這點在十年前就已經很明確。我認為這個國家會持續向資本主義邁進,它如果不這麼做,逐年就會虧損更多。國外已經有愈來愈多投資者想要進入烏克蘭的市場,它勢必得接受資本主義,不過它應該會比較偏向歐式資本主義,而非美式。」
我問:「烏克蘭近年有無任何正面發展?」
「烏克蘭人現在對世界比較熟悉了,很多人都去過埃及、土耳其、奧地利、波蘭和西班牙,他們甚至有自己的廉價航空公司。城市地區的年輕人普遍都會使用網路,大家若不是本來就會說英語或正在學英語,就是在自責為何沒學英語。」
烏克蘭確實希望成為東歐的瑞士─中立、和平又繁榮。蘇聯解體時,烏克蘭擁有世界第三大的核武庫,並將軍隊裁減了一半,因為英美俄答應擔保它的安全。如今俄羅斯已背叛此約定,英美會願意守信到什麼程度?別太指望他們。

試想如果美國攻打了加拿大,換成俄羅斯來支援加拿大,美國會不惜一切求勝,但俄羅斯絕對不會那麼投入,因為戰場不在他們的後院。這就是為何美國不會冒著全面核戰的風險去救烏克蘭,俄羅斯也知己知彼,所以它終究會挖走烏克蘭境內俄裔族群比例最高的區域(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當年俄羅斯吞併阿布哈茲(Abkhazia)和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就是遵循這個劇本,外聶斯特里亞也是類似的故事。假如普丁的白俄羅斯奴才盧卡申科被一位反俄人士取代,普丁也能以「保衛俄裔同胞抵抗納粹殲滅」為藉口侵占白俄羅斯。
話說回來,雖然俄羅斯擴張了領土,它也跟一位朋友反目成仇。試想美國攻占魁北克的後果,美加關係至少會烏煙瘴氣一百年。更甚者,普丁也驅使原本的中立國(例如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非但沒有遏止烏克蘭加入歐盟,反而將它推向歐盟的懷抱。普丁耗費資源征戰,結果只不過讓俄羅斯的面積增加了可悲的千分之三。未來的俄羅斯人不會記得普丁的德政,只會視他為暴君。
如同土耳其,烏克蘭曾經試圖跟俄羅斯和西方同時維持良好關係,但戰爭終結了這如履薄冰的舞步。烏克蘭還是有可能回歸中立,就像二戰後奧地利選擇以中立換來自由,這場戰爭最終的協定也可能會要求烏克蘭維持中立。或許到了二○三○年代,烏克蘭將仿照奧地利加入歐盟,但不會介入北約。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仍會感嘆自己失去的國土,但他們應當轉移焦點,將烏克蘭轉化為東歐的經濟龍頭。烏克蘭擁有卓越的科技人才,足以使它搖身變成未來的人工智慧和軟體樞紐,而俄羅斯可能還苦蹲在頓巴斯挖掘煤礦。
烏克蘭人能教我們什麼
多使用小型巴士:烏克蘭到處都有小巴,它兼具計程車和公車的功能。美國人很少以這種輕便型休旅車作為大眾交通工具,我們常看到一輛巨大巴士只載著兩三個人,不僅浪費能量又製造空氣汙染,實在可悲。旅行社應該把大型車保留給熱門路線,用休旅車跑冷門路線。請你的市政府做些變革。
培養並經營深遠的友誼。在這個數位時代,人際關係已經變得膚淺而短暫。盡量與你的朋友親身互動,鼓勵他們當個不速之客,拋棄面具,分享內心的真實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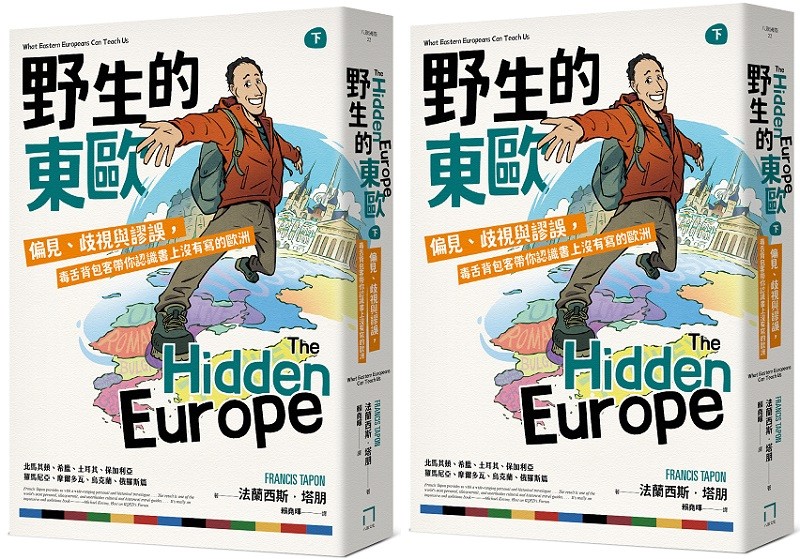
*作者法蘭西斯.塔朋(Francis Tapon),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高材生的他畢業後不但沒有進華爾街投資銀行工作,反而踏上歐亞大陸進行壯遊,永遠改變了自己的人生。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野生的東歐》下卷(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