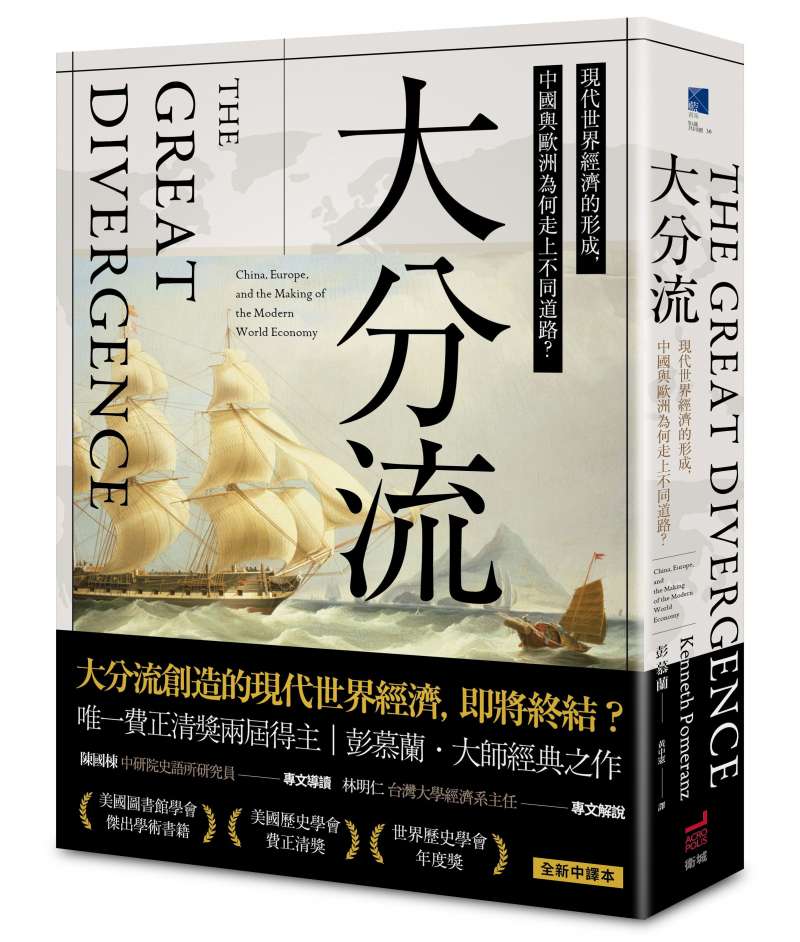「一旦你開始思考經濟成長,就很難想別的事情了。」
──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在十四世紀生活水準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是如何被以英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過去兩個世紀藉工業革命之力,高速成長反超車的?」這個大哉問,一直是史學界與社會科學界最歷久彌新的核心議題。傳統的西方中心論強調早在十五世紀英格蘭與荷蘭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就已經超越中國。而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在技術、文化與制度上的各項先備發展,也都讓工業革命的產生,看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反觀中國雖然有過如火藥、紡織、造紙等領先全球的技術,在明清時代(可能)也出現過所謂萌芽階段,但資本主義卻始終未在中國生根。根據傳統的說法,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市場運作並不健全,而農業產出的增長,也只是透過密集的勞動投入而來,並未將剩餘的勞動力與資金移出農業部門,只能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陷阱中打轉,自然無法進入現代經濟成長的階段,此即黃宗智所謂的「內捲化」之說。[1]
彭慕蘭的《大分流》一書,便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底下,從GDP 的計算、對歐洲與中國更細緻的制度比較、以及歐洲所面臨的機運下手,論證作為當時學界主流的傳統歐洲中心論假說,並不足以解釋歐洲與中國的大分流。可以想見,在本書出版之後,一定會有許多各領域的學者對他的資料跟論點提出批評。本篇解說分別對《大分流》一書中論點的反思,以及分流成因的各家觀點,對讀者作提綱挈領的說明。
到底誰算錯了?
在《大分流》的第一章跟第三章,彭慕蘭利用了許多統計數據,說明中國在出生率、科技、交通、奢侈品等方面,與同時期的英國相差無幾,並認為大分流的時點大約在十八世紀中期,遠晚於當時主流學說的看法。
對於這個大膽的論點,最新的研究有許多批評。布羅德拜瑞(Stephen Broadberry)是牛津大學的經濟史教授,也是《經濟史評論》期刊的主編。他在二○一五年的文章(Broadberry 2015)認為,加州學派的中國數據應屬高估,大分流並沒有像《大分流》強調的那麼晚發生,不過這篇文章肯定了《大分流》一書的另一個貢獻,便是其強調了「地區差異」。布羅德拜瑞發現,在歐洲內部其實有許多小分流:義大利先超過了西班牙,荷蘭後來居上,最終由英國的工業革命超越了其他歐洲國家。亞洲則有日本後來居上中國的小分流。而他認為黑死病與貿易路線的擴張是解釋這些小分流的重要因素。布羅德拜瑞、管漢暉與李稻葵(Broadberry, Guan and Li 2018)則提出大分流的分界點應始自蒙古南下。根據他們的估計,北宋的人均GDP 超過一○○○美金,高於歐洲的七五○美金。卻在一三○○年(元朝)時開始落後,於明清鼎革後,GDP 便開始快速衰退,而且是全面性的。這現象已經不能單純地用中國的地區差異來解釋,而是跟制度的變化有很大的關係。
彭慕蘭在二○一一年的文章〈回覆與再思考〉(Response and Reconsideration)中,承認他高估了一些中國資料,以致於把大分流的時間估計的稍晚,然而他也說的確有不少後續研究是支持他的論點的。但無論如何,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一個研究,會直接宣稱在一五○○年的時候,英國跟荷蘭的發展遠遠超過全世界其他地方。就如同布羅德拜瑞等人所言:一三○○年時中國與西方最富裕的地方發展相當應是一個合理的猜測,但在一七五○年之後,雙方差距就已經大到無法用地區差異來解釋了。這個時間點,也是在我們所認知的工業革命之前(Broadberry, Guan and Li 2018)。
在這裡特別要提醒的讀者的是,計算GDP即便在現代都是一個細瑣繁重的工作,更遑論斷簡殘篇的古代資料處理有多複雜。因此在對這些資料作詮釋時,一兩百美金的差異,很可能是落在測量誤差(measurement error)範圍內。陷在這些枝節的計算比較過程中,可能會讓我們見樹不見林,忘記了更重要的問題:大分流為什麼會發生?
下圖一畫出了英國、法國、中國、日本跟台灣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資料取材自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ison)的「麥迪森計畫」(Madison Project)。[2]縱軸是取了對數之後的GDP ,因此下圖斜率在數學上其實就是經濟成長率。從下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一七○○年之前,這幾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互有超前。接著英法兩國開始緩步上升,中國則些微下降。但在一八二○年之後,英法兩國經濟成長率開始大幅提升,百年之後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就已經來到英法六○○○美金比中國的六○○美金!另外,日本在明治維新、台灣在日治時期之後,也都開始了高速的成長。換句話說,在十七世紀之前,東、西方的生活水準,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十八世紀中葉後,西歐開啟現代經濟成長模式,到了二十世紀初,已經把東方遠遠甩開!當看到此時東、西方的差異如此巨大,爭論十六、 十七世紀東、西方到底誰比誰高出一兩百塊美金,反而就顯得荒謬了起來。換句話說,所有的歸因討論與對當時資料的詮釋,都得要對一八二○年後的大分流如何產生鋪路,提出假說加以論證,才是正途。
成長是運氣還是制度?
經濟成長其實就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起點,畢竟祖師爺亞當.斯密都已經把書名定成《關於國家財富的本質與後果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了!而依據國民所得之父,一九七一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的定義,經濟成長是「社會脫離傳統農業經濟,平均每人GDP成長率持續大於零,平均每人GDP水準逐年上升的現象」。除了GDP的持續成長外,生產力的增加、經濟結構的轉變、社會對事物的看法、意識形態的調整、市場化及世俗化、技術創新的速度,也是庫茲涅茨所認為的重要指標。他也更進一步提出,國家要能進入現代經濟成長的階段,上述這些指標與該國過去或其他尚未進入此一階段的國家相比,都得要有數倍以上的成長才行(both large multiples of the previous rates observable in these countries and of thos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3]以此觀之,圖一的西歐英、法兩國在一八二○年就符合了這個標準。日本在一八七○年,台灣則是在一九一○年,而中國則要到一九五○年之後才開始現代經濟成長。
雖然《大分流》花了不少篇幅論證,即便在一八二○年,江南與英格蘭的生活水準是相當的,並接著強調資本主義在英國發生純粹只是機運,尤其是「新大陸市場」的發現跟「煤炭」的開採時,會讓讀者有: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本書論點居然是「英國佬只是運氣好而已!」之驚嘆。但其實《大分流》並未忽略制度的角色,只是彭慕蘭對於制度的看法比較微妙(subtle)。他反對的是當時所盛行的「歐洲有健全運作的市場,中國則沒有」的觀點。他比較了同時期中國跟歐洲各國的土地制度,發現歐洲許多地方不允許土地自由轉讓,反而在中國,千年土地八百主,土地自由轉讓是常態。他也比較了中國與歐洲的勞動市場,反對黃宗智所提出的「內捲化」假說,即中國陷入了人口壓力跟農地面積過小的惡性循環,中國農家為了顧及生存,只能大量將勞動力,投入到勞動密集的小農經營上,導致邊際勞力產出持續遞減,乃至利潤趨近於零。彭慕蘭花了許多篇幅說明當時中國人的娛樂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 of leisure),他認為,如果中國當時真的像黃宗智所說的,過度投入於勞動上,並會過度減少娛樂,那史家又該如何解釋明清發達的娛樂呢?
那彭慕蘭認為什麼制度在歐洲很重要?當時的主流學說強調歐洲「看不見的手」,但彭慕蘭卻認為歐洲比中國多出的是「看得見的手」。大規模的殖民地與新市場,是中西顯而易見的差異。兩方的政府對於海外貿易的態度則是造成這差異的主要原因。歐洲的政府透過特許、軍事等手段,協助歐洲的私人企業開拓了海外貿易並從中獲利。儘管中國也有鄭芝龍等盜商合一的海上集團,但在歐洲的海外發展裡,政府與公司之間緊密地合作,是明清中國所沒有的。
彭慕蘭進而將這種差異,歸諸於中國與歐洲列國政治環境的不同:歐洲列國的海外拓殖,其實是歐洲內部軍事競爭的延伸,至於中國的朝廷,從未許可中國的海商集團在海外有排他性的權利。也可以說彭慕蘭雖然強調「機運」 的層面,卻也相當小心地考量了海外市場與歐洲特有的政治與制度的關係。簡言之,彭慕蘭反對把大分流的差異歸因於「中國的市場先天不良於行」的解釋,進而去尋找真正可造成差異的解釋(non-trivial explanation)。
史學界的迴響:從土地交易制度出發
《大分流》在經濟史界產生了巨大的迴響。出版後不久,在書中被他批評的主要學者,很快地提出了回應。許多不滿意「機運說」的學者,也提出了許多新的假說,主要集中在制度上面。以下我們就一一說明。
首先,黃宗智立刻回文為他的「內捲化」理論辯護(Huang 2002)。他認為十八世紀江南農業仍是勞力密集的,而同時期的英國卻已經轉成了資本密集的農業。彭慕蘭(Pomeranz 2002)的回應認為,黃宗智說得對,英國的確有比較多資本密集的農業,但《大分流》的主要論點是:你不可能只用中國的勞力過度密集來解釋大分流本身。兩方的辯論當然沒有結論。
不過在《大分流》出版的前幾年,黃宗智便將研究的注意力轉向晚清到民國的法律;而在《大分流》出版之後,他的研究更是集中在清代到民國初期的收養、婚姻、勞動、土地買賣等中國傳統的法律制度。在這一輪的研究裡,黃宗智對中國傳統的制度仍多有批評,但也強調他的研究不是要說明中國與西方的法制 「誰優誰劣」。而在《大分流》出版後的兩年,黃宗智便退休了,於是將中國傳統的法律制度與《大分流》連結起來的工作,則是要等到於今年(二○一九)在耶魯法學院拿到終生聘任的張泰蘇來完成。
張泰蘇大學在耶魯主修數學跟歷史,後來在耶魯獲得法學博士與歷史博士,現任教於耶魯法學院。他博士論文的問題意識,便是想要將中國傳統制度的缺陷,和《大分流》的議題連結起來,這也是他最近出版的《儒家的法律與經濟學》(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的主題。張泰蘇觀察到英國於中世紀之後,在土地法律上,有讓產權明確化的趨勢,反觀中國的土地契約,卻從明清時期開始,發展得越來越複雜。舉例來說,中國的「典契」讓把土地「典出去」的人,可以在未來的任一時間,把土地「贖回來」,張泰蘇認為典契會讓想要收購大片土地的買家卻步,阻止了整併土地的規模經濟。
張泰蘇因此推論「典契」會讓被交易的土地零碎化,不利於土地集中。而有規模經濟的經營農場不易產生,則是江南農業生產力逐漸落後於英國的主因。至於中國法律何以會發展出「典契」,則跟中國的儒家文化有關。儒家文化注重 「長幼有序」、「論資排輩」,所以地方的風俗傾向保護「又老又窮」的小地主,導致年輕又富有創業精神的年輕買家無法「圈地」,將土地整併成現代的經營式農場。這可以說是「內捲化」理論被批評之後,重新省思了中國傳統的制度,提出了「內捲化2.0」的新解釋。而從一開始只強調小農勞力密集的內捲化假說,到更進一步思考 「是什麼文化跟制度導致了中國的農業型態跟英國不同」,這問題意識的改變,便是由《大分流》所推動的。
經濟學界的迴響:從制度出發
由艾塞默魯(Acemoglu)和羅賓森(Robinson)兩位所著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應該是近期制度經濟學的扛鼎之作了。他們提出廣納型(inclusive)制度跟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的分別,認為歐洲得以發展的原因,主要是能夠制定出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經濟上開放機會的廣納型制度。他們也結合許多歷史事實,用了許多篇幅討論哪些因素可以支持廣納型制度的發展,以及國家如何透過制度避免菁英破壞正向回饋,邁向良性的循環,而非走回榨取的老路。在他們的書中,運氣(如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提到的地理說)從一開始就是他們要反對的論點。[4]
另一位提出不同看法的則是在史丹佛大學任教的格雷夫(Avner Greif),他喜歡用賽局理論解釋歷史現象,研究的一貫主題便是中世紀以來歐洲商人,或環地中海地區的猶太社群,如何發展「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來促進貿易。在他二○○六年出版的專書《制度與通往現代經濟之路:中世紀貿易的教訓》(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中,便特別回應了彭慕蘭的看法。他認為就算在十八世紀的時候,中國與英國的經濟表現雖然在統計上極為相近,但是在商業組織的制度上,卻早有所不同。格雷夫認為歐洲從中世紀晚期以來,便開始發展出「既非國家,亦非血緣」(neither the state nor kinbased)的社會組織,這些制度是為了解決合作問題刻意設計出來的。
後來在二○一七年另一篇與塔貝里尼(Guido Tabellini)合著的文章裡,格雷夫更進一步探討中、西在社會組織上的不同。他們認為,歐洲從中世紀以來依靠的是自治城市,中國從宋代以來卻是依賴宗族。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供給公共財或其他財貨時,促進合作所需的執行成本(enforcement)的性質有所不同:宗族內部的執行成本較低,但是西方的方法,在建制好之後,卻更可以擴大履行對象的範圍(scalability)。換句話說,中國選擇了一條一開始比較簡單,固定成本投入較小,但日後發展較為困難的捷徑,西方則反之(Greif and Tabellini 2017)。
另一位對《大分流》提出意見的,則是在西北大學經濟系任教的莫基爾(Joel Mokyr)。普林斯頓大學出版《大分流》時,是將其歸類於「西方史」(Princet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而非「中國史」,而這西方史系列的編輯,就是莫基爾,他也是彭慕蘭謝辭裡特別感謝的對象之一。《大分流》在提及英國工業革命與說明大分流時間點時,也特別引用莫基爾的「全面改變生產過程的發明」(Macro-inventions)的概念。彭慕蘭認為,在一七五○年以前,西方在此時並沒有比中國多了多少,因此在土地制度與技術創新都沒太大不同的情況下,很難解釋大分流會在一七五○年以前發生。
不過莫基爾本人並不同意這樣的解釋。莫基爾(Mokyr 2015)在書評中提到,加州學派為了避免西方中心論,不喜歡談論文化的優劣。但是對他來說,文化跟制度是最重要的。莫基爾在二○一六年出版、統整其近年想法的專書《增長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中認為,西方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之處,正是來自於有競爭的思想市場(Competitive Market of Idea)。[5]
莫基爾在該書中提出了自己的大分流議題:為何在西元一二○○年,西方還是一堆野蠻人所處的原始世界,而中國的宋代則是知識的黃金年代。但只經過短短三百年,中國的文人如徐光啟卻感受到西方有些知識已經超過中國,而積極與耶穌會交流?乃至西元一七○○年後,西方如牛頓、亞當.斯密、休謨等科學哲學家相繼大放異彩?更特別的是,西方傳統的「正教」(orthodoxy)或既得利益者,當然也想要抵抗這些新觀念的發展,但是在「啟蒙時期」(Age of Enlightenment),新觀念又是如何如願打倒舊勢力?
啟蒙可說是西方獨有的現象。德先生跟賽先生得以在西方站穩腳步,跟啟蒙運動的勝利有關。[6]相對的在東方,清代文人也開始了考證運動,批評舊的知識,卻沒有帶來西方啟蒙運動的效果。莫基爾認為,這是出於知識的市場在中西運作大為不同的緣故。在中國,精通數學沒有辦法讓學子得以通過科舉,但是在西方,從「文人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這一類的跨國文人社群成立以來,文人專精數學、發明新的定理,可以在同儕當中得到聲望。一旦名氣大了,便可以得到私人或官方的贊助,這些贊助讓西方文人可以溫飽,更可以替他的新見解添加了權威,因為審查人通常都是學界內資深的學人。[7]在書中,他更仔細地舉例這樣的贊助制度,讓牛頓他們這些「天才」如何辛勤工作。當然中國也有贊助制度,卻是壟斷在帝王手中,當帝王對新知有興趣的時候,知識可以突飛猛進,但是事在人為,當帝王失去興趣,或是換了皇帝,研究便可能停滯甚至倒退。
莫基爾(Mokyr 2016, Ch.11)則對「西方為何有競爭的思想市場」進一步提供了解釋。「思想市場的自由競爭」觀點可以追溯到書中不斷引用的休謨(David Hume),而休謨本人就認為政治分裂的局面導致的列國競爭是一個因素。莫基爾給了兩個理由,說明政治競爭如何加強思想市場上的競爭:第一個是不同國家會想要競爭最好的公民來增加實力(這一點與李斯的〈諫逐客書〉不謀而合),第二個則是保守勢力「協調失靈」(coordination failure),也就是保守勢力彼此分裂,無法一起來壓制新觀點。而中國就是一個最好的反例,因為大一統的帝國沒有協調失靈的問題,科舉考試,本身就可以決定什麼知識有用、什麼知識沒用,所有的國民也服膺「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文化價值,整個國家就也形成一個千年不變的超穩定結構。
莫基爾更進一步強調政治分裂對於知識競爭的效果,不只是國家與國家間的競爭。政治分裂的另一個結果是歐洲生產知識的團體,或是文化創業者(cultural entrepreneurs),時常是國家之外的獨立機構。早期的修道院,後來的大學,獨立運作的行會,乃至自治的城市,常常都是新知識的來源,國家要想辦法跟他們競爭或合作,但這些團體不是國家的一部分。在二○一七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QJE)的文章當中,莫基爾便與另外兩位經濟學家德拉克羅瓦(David de la Croix)與狄歐普克(Matthias Doepke)共同提出了總體模型跟數據專門處理行會(guild)對於默會致知的知識(tacit knowledge)傳播的效果(De la Croix, Doepke, Mokyr 2017)。
若將中國的科舉制度拿來與莫基爾所言,用以鼓勵文人證明、創新跟發明的西方制度相對照,其後果就很明顯了。十年寒窗如果成功,收益是如此之大,導致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個成功率不高但獎金很高的錦標賽(tournament)中。事實上,這些年輕人並非缺乏聰明才智,香港中文大學的白營(Bai, Ying)與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任教的賈瑞雪(Ruixue Jia),在二○一五年的研究就發現,在科舉廢除後,中舉比率越高(代表人力資本越高)的地方,參加後來革命黨活動的比例越高,同時擁有現代人力資本成立新式西方事業或出國留學的機率也越大![8]
整體來說,經濟學家利用賽局模型與計量技巧,以歷史事件作為詮釋的藍本,討論各方利益相關人(貴族vs國王,貴族vs創業家)如何在既有的政治經濟誘因結構下作選擇,以及他們會如何試圖改變這些誘因結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若能產生出較能融合各方利益的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經濟成長就可能發生。在此一大架構之下,比方如何跳脫宗族為主的傳統治理、轉向以數字為基礎的現代治理,如何處理破壞性創造所產生的社會後果等等機制(mechanism),應該會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社會學界的迴響:中國不可能在十九世紀發展出資本主義?
《大分流》出版後,最不能同意該書結論的,恐怕是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的趙鼎新了。他直截了當地說:「中國在十九世紀或此前或稍後的任何時候,都沒有可能出現工業資本主義方面的根本性突破。」(趙鼎新,2014)
他認為,即便明清時期江南有較高的生活水準,但「技術創新並沒有鼓勵性的回報,科學方法/理性極不發達;最重要的是儒法合一的新儒家意識形態沒有面臨重大的挑戰,商人也無法利用他們的財富來獲取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從而抗衡國家的權力。」(趙鼎新,2014)這與西方有很大的差別:西方不論是宗教、政治、封建領主、商人、城市工匠行會等各階層的菁英,都長期處在與其他階層鬥爭的狀態之下。沒有人能夠長期保有穩定的權力,因此菁英的面貌,在不同的地區與時間是不同的。再加上歐洲長期存在著多國/多地區的競爭狀態,使得制度競爭成為一個可接受的概念,修改制度後所帶來的好處,也會多次地出現。但對傳統中國來說,儒家對統治基礎提供正當性,法家則提供如何使用權力的操作手冊。皇族加上數量龐大的官僚系統一起統治中國,換個朝代之後,整件事情重來一遍,唯一不變的,則是菁英的面貌。總而言之,帝制與內向的國家權力永遠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或者用總體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恆定狀態(steady state)。[9]
換句話說,歐洲人在政治行不通的時候,會思考制度的設計哪裡有問題,但中國人則只能如「大旱之望雲霓」,期待明君的降臨。這樣的制度,對在資本主義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商人來說,基本上是相當不利的。缺乏意識形態支持,也沒有很大政治跟經濟權力的商人,從來就不是帝國要捍衛的對象。讀者可以想像,如果你是胡雪巖,賺來的錢是投資在「浙江鹽大使」政府獨占事業並買官比較保險,還是投資海外新航路冒險或新技術開發比較划算?
《大分流之外》與《大分流》之後
彭慕蘭在二○一一年回應了文獻在《大分流》出版十年後的發展,並回應了同刊號其他文章的批評,也談及了他認為《大分流》一書較弱的地方跟貢獻。他同意科技跟知識傳播的討論是書中最弱的部分,因為他當時缺少足夠的資料去說明這一部分。而他的確也高估了一些資料,大分流的時間應該還是要再提前。
另外,加州學派的健將王國斌(Roy Bin Wong)與加州理工學院的羅森塔爾(Jean-Laurent Rosenthal,經濟學家、歐洲經濟學史家)在二○一一年合寫了《大分流之外》(Before and Beyond the Divergence),除了回應許多批評,也對加州學派的觀點提供了經濟學模型與制度變遷的解釋。他們認為,關於探討中國土地制度發展不良的文獻,比如說土地典賣、回贖的現象,在歐洲許多地方也很普遍。類似於格雷夫所說(Greif 2006)的商業組織,在中國也是存在的,而中國也發展了許多非正式組織去協助長程貿易。
不過他們也同意大分流的差異,可以追溯自一五○○年左右,尤其是對知識創新所提供的制度支持,很可能是主因。他們主要的假說也跟歐洲政治分化、中國大一統有關:中國在承平時期,大量的製造業勞力是分散在鄉村,歐洲則因戰爭頻繁,需要有可以關上大門的城市,用中國人習慣的用語來說,明清的中國是搞「鄉村企業」,歐洲因為頻繁的戰爭所以是搞「都市企業」。長年的戰事讓歐洲陷於長期的貧窮,但企業為了躲避戰爭,有誘因遷入城市,在城市中面對較高昂的勞力價格跟相對較低廉的資本價格時,這些企業進一步就有誘因發展出節省勞力的技術(labor-saving technology),這便是工業革命的前身。[10]他們以此解釋了為何宋代有製造業科技水準較高的現象,因為宋朝戰事最為頻繁,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少數的城市,因此有了與歐洲城市製造業的技術進步相當類似的先決條件與發展過程。[11]彭慕蘭在書中,沒有特別談論歐洲的政治情勢、軍事對於新科技的影響,不過《大分流之外》補足了這一塊。
最後,彭慕蘭在回應趙的評論時,也認為「他的確指出我忽略的問題」。而他也正在寫一本新書針對這些批評作出回應。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大分流2.0」可以帶給我們更多知識上的辯論。[12]
結語
研讀《大分流》,可以有兩個不同的切入點。一個是學術的,不論是從歷史材料的蒐集,農家生活水準的計算,到東西方土地制度、新創制度、宗族與現代政府提供公共財、乃至市場競爭的比較,都可以讓我們更瞭解人類生活互動的過程,以及制度跟各種機制從中所扮演的角色。
對彭慕蘭來說,雖然許多人針對他的論點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之後大家開始提出新的解釋,並與他的資料與說法對話,這是他當初寫作的重要目的。學術研究,永遠是希望大家開始討論大分流為何發生,而不是在假設知道答案後,才開始研究大分流。從激起討論的角度來看,《大分流》是成功的,而這些論點的相互激盪,也正是莫基爾所說的「有競爭的思想市場」的最佳例證!若能從這些討論連結到本土議題,如台大法律系王泰升老師的《去法院相告》便討論到,臺灣從「包公判案」的清代,過渡到了日治時期的近代西方式法院,臺灣人如何在這變遷中利用法律制度來解決紛爭;或如台大經濟系吳聰敏老師對大租小租權的研究,以及古慧雯老師對典契的研究,也都可以讓我們更瞭解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歷史。
另一個切入點毋寧是更入世的,從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的角度去看。現在的台灣,如果能更加開放思想的競爭市場,更往數字管理的方向發展,更強調以證據為本的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evaluation),並且對於創新的市場給予更大的寬容(整體來說,便是建立更包容的政治經濟制度),那台灣的發展,將與沒做這些有多大的不同?
林明仁為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鄭紹鈺為台大經濟系碩士班研究生
本文選自《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衛城出版)。
註解
[1]有關黃宗智的內捲化理論,請見黃宗智(1985)跟黃宗智(1990)。
[2]圖一使用的資料來自於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version 2018,並請參考Bolt, Inklaar, Jong, and Zanden (2018),“Rebasing ‘Maddison’: new income comparisons and the shape of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10。對於「麥迪森計畫」這一個長期計劃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麥迪森(2007)。
[3]請參考庫茲涅茨(1966)跟庫茲涅茨(1973)。
[4]有關於他們對彭慕蘭《大分流》的直接回應,請參考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
[5]莫基爾(2015)這篇雖然是書評,但其實這篇文章有一半是摘要莫基爾(2016)。
[6]莫基爾這觀點似乎也可以用來思考中國的五四運動:中國為在進入民國之後,想實施西方的制度卻百般失敗,仍要發動一場五四運動邀請「德先生」跟「賽先生」到中國來。周策縱便認為傅斯年等新興的知識份子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其目標便是要「走向大眾、啟蒙大眾、組織大眾」(to go among the masses of people, and enlighten and organize them)(Chow 1960)。余英時近年的文章(Yu 2016),則強調五四運動跟西方啟蒙運動仍存在了一段不小的差距,特別是指出傅斯年他們沒有西方經歷啟蒙時的「文人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莫基爾(2016)認為「文人共和國」這個社群,在西方啟蒙運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社群的存在,讓歐洲知識份子得以一邊彼此競爭,卻又可以透過「文人共和國」來協調彼此的合作(coordinate)。若我們接受莫基爾的觀點,則中國在五四運動時,並無這樣的社群,或許這可以說明,為何五四運動帶給中國的新觀念,一如余英時(Yu 2016)所指出的,常常彼此分歧,有時甚至互相衝突。
[7]審查一事,出於他書評中對自己見解的摘要,見 Mokyr (2015, p.99): “Patronage depended on the evalu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senior scholars.”。
[8]有關於廢止科舉後對於革命黨的影響,請參考白營與賈瑞雪(2016),廢除科舉後與成立新式西方事業的關係,請參考白營(2014)。
[9]有關趙鼎新關於大分流文獻的意見,請參考趙鼎新(2015),特別是第十三章“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10]他們的假說認為戰爭改變了資本價格跟勞動價格,因為改變了創新的型態,不過他們對戰爭本身的看法是負面的,並認為莫基爾的「啟蒙假說」忽略了啟蒙的代價是包括宗教戰爭在內的大小戰事。
[11]莫基爾(Mokyr 2015)不同意王國斌與羅森塔爾(Rosenthal and Wong 2011)的推論,認為這只是某種「要素價格」理論的變體,一如彭慕蘭在《大分流》中引用的莫基爾的學說,莫基爾一貫的論調便是「要素價格」只有改變創新的型式,而不會影響創新的程度。集中在都市,只是有利於節省勞力的創新,集中在鄉村,也可以發展有利於使用勞力的創新。
[12]二○一五年時彭慕蘭接受中國《澎湃新聞》的記者楊松林的訪問,標題為〈彭慕蘭獨家回應《大分流》爭議:趙鼎新指出了我忽略的問題〉。
參考書目
趙鼎新(2014)。加州學派與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學術月刊,46(7),157– 169。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3),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ooks.
Bai, Ying (2014), “Farewell to Confucianism: The Modernizing Effect of Dis- mantling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orking paper,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i, Ying and Ruixue Jia (2016),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 Econometrica, 84(2), 677–733.
Bolt, Jutta, Robert Inklaar, Herman de Jong,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2018), “Rebasing ‘Maddison’: New Income Comparisons and the Shape of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GGDC Research Memorandum, 174.
Broadberry, Stephen (2015),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Divergence,” working paper.
Broadberry, Stephen, Hanhui Guan, and David Daokui Li (2018),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980–185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8(4), 955–1000.
大分流 450
Chow, Tse-tsung (1960),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De la Croix, David, Matthias Doepke, and Joel Mokyr (2017), “Clans, Guilds, and Markets: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1), 1–70.
Ellickson, Robert C (2012), “The Costs of Complex Land Titles: Two Examples From China,” in Brigham-Kanner Prop. Rts. Conf. J. vol. 1, HeinOnline, 281.
Greif, Avner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eif, Avner and Guido Tabellini (2017), “The Clan and the Corporation: 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5(1), 1–35.
Lucas Robert E.,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3–42.
Huang, Philip C (1985),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 501–538.
451 解說 為什麼中國沒有資本主義?《大分流》之後的反思
Maddison, Angus (2007),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c Foundation.
Mokyr, Joel (2015), “Peer Vries’s Great Divergence,” Tijdschrift voor Sociale en 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12(2), 93.
—(2016),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 539–590.
—(2011), “Ten Years After: Responses and Reconsiderations,” Historically Speaking, 12(4), 20–25.
Rosenthal, Jean-Laurent and Roy Bin Wong (2011),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Yu, Ying-shih (2016), “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 in Josephine Chiu-Duke and Michael S. Duke (eds.),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eventeenth Century Through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Columbia UP, 524–574.
Zhang, Taisu (2011), “Property Rights in Land, Agricultural Capitalism, an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Pre-Industrial China,” San Diego Int’l LJ, 13, 129.
Zhao, Dingxin (2015),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