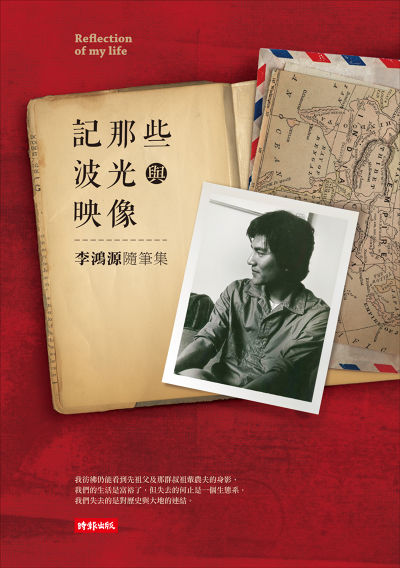台南,第二個故鄉
我的命中與「水」總是脫離不了關係。
出生時先曾祖父李浩生公找了當時台北大橋頭著名的命理大師葉秀春先生,幫我批了八字。他說這小孩什麼都好,就是命中缺水,因此命名時在名字中有了六點水。但看來似乎還不夠,最終還必須選擇水做為終身志業。
我的初中是在台北盆地的另一端,一所私立中學「大華中學」就讀。我是九年義務教育開始實施的第一屆。理論上應該念泰山國中,但家人不放心讓我讀一所新設立的學校,於是我們許多功課較好的同學都去報考私立學校,在錄取的幾間學校中,我選擇了大華中學。
這是所座落在吳興街底,拇指山下的小型學校。地點非常偏僻,四周稻田圍繞。我每天一定要搭上六點鐘從泰山發出的第一班公路局公車,到台北車站後,再轉半小時才有一班的三十七路公車,以確保趕上七點半的早自習。
大華是所學生多來自高級官員及經濟條件優渥家庭的「貴族學校」,我大概是少數在家長職業欄填上「農」的學生,也因此常隱約感覺老師擔心我付不出學費。幸好我是個用功的好學生,加上媽媽每天把我打理得整整齊齊,三年下來也和同學處得相當融洽。
學校的老師臥虎藏龍,來自大陸大江南北,印象中在教學上非常認真,而且對課業的要求嚴格,我也因此打下深厚的英數理底子。回想起來,這三年是我一生中功課最好的一段時間。
記得高中聯考放榜時,我的分數比建國中學的錄取標準還多了足足有五十分。我們一班五十多位同學,有一半都進了建國中學,其中六個又和我分在同一個班級,當了六年的同班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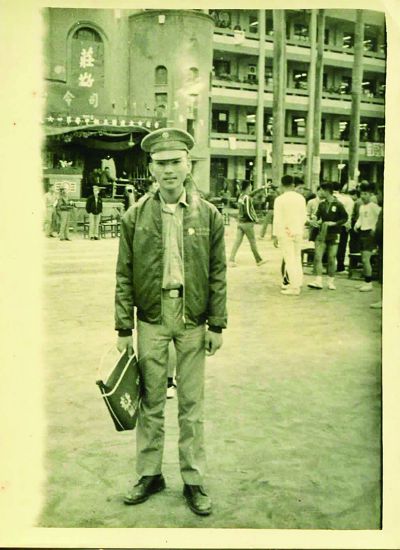
建國中學是所歷史悠久的名校,有棟日治時期留下至今,造型典雅的老舊磚造建築,我們稱之為「紅樓」,以及一座一起風即吹起飛沙走石的操場,我們稱為「沙漠」,因此建中學生常以刻苦耐勞的「駱駝」自居。因為特殊的微氣候條件,小型龍捲風是建中操場的特產,常常可見到漏斗形狀的漩渦捲起陣陣黃沙,越過半個操場,然後在一片驚呼聲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個學校的學生除了會讀書之外,更出名的是號稱「黑衫軍」的橄欖球隊,驍勇善戰、所向披靡,揚名國內。記得高一要去學校報到時,家人(尤其是祖母)除了喜悅又驕傲外,最擔心我會去參加橄欖球隊,因此三申五令,絕對不可以碰橄欖球。
就我記憶所及,當年建中的師生關係很平淡,老師很多是補習班名師,但白天在課堂上教得並不起勁,大概精華的內容要留到晚上在補習班上。同學平常都是自己讀書,而且私下暗自較勁,在學校時都故作輕鬆拚命玩,放學後再拚命苦讀。那時的高中生活非常平淡,三年的週末就在打球、打橋牌、下棋及郊遊中度過了。
事實上,我們這一屆畢業生在後來出了好幾個「名人」。我還在內閣時,經建會主委管中閔、研考會主委宋餘俠、國科會主委朱敬一都是同班或隔壁班同學,其中管中閔更是從初中開始,一路都和我同學。
建中的同學中,最特立獨行的就是後來寫了《拒絕聯考的小子》的吳祥輝。他讀的是二十六班,他們班上有幾個人和我是初中及小學同學,當時我經常去串門子。高三時大家都拚得要死要活,就他一個人擺明不考大學聯考,常常是全校師生看著他一個人在操場踢足球,即使下大雨也照踢不誤。
高中時,我每天坐三重客運公車到中華路國軍文藝中心附近下車,步行一段路後穿過植物園到學校,每天走兩趟,一走就是三年,因此對植物園的一草一木及四季景色變化有了深刻的觀察。直到現在,園內的每棵大樹的位置和樹名,我都還記得清清楚楚。
偶爾我們也會繞道走重慶南路,說是為了「逛書店」,但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去看北一女的女孩子。那是一個民風保守的年代,沒人敢上前搭訕,只要遠遠地看著,就可以讓幾個小男生興奮地談論好幾天。
當時的重慶南路是條充滿大小書店及濃濃文化氣息的道路。每家書店所賣的書不盡相同,成為我在回家途中最常駐足的場所。濃濃的書香、精彩的各國圖書,令人流連忘返,無形中也養成了我這一生最好的嗜好,買書與讀書。
三年的高中生涯,我一直自認成績還不錯,總以為考上台大、清華,一定沒問題。但做夢都沒想到,大學聯考放榜,我居然只考上成功大學,而且還是冷門的水利工程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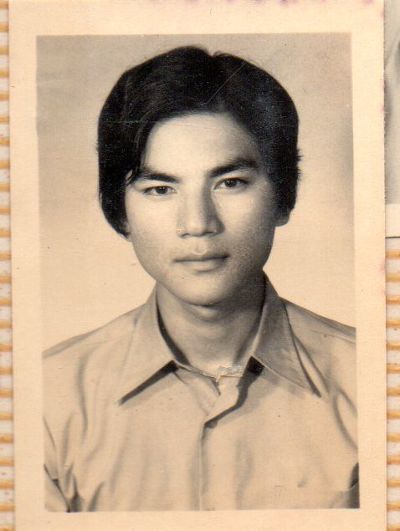
從初中開始,我的英文底子就打得很好,高中成績也不錯,但聯考居然只考三十分,「背書」一直是我最拿手的本事,三民主義也僅拿到六十八分,幾乎不可能發生的「慘劇」全碰上了。
活到十八歲,我一輩子沒去過濁水溪以南。台南在哪兒?成功大學是所什麼樣的學校?我毫無概念,但既然考上,也只有硬著頭皮去報到。
我有一個從初中到建中都常在一起的同學薛智文,也考到成功大學,於是他的爸爸帶著他,我爸爸、媽媽帶著我,大家拖著沉重的行李,在報到前一天南下成功大學。
還記得事前我們聯絡建中校友會,對方說會有學長帶「板車」來幫忙拉行李。於是我們搭上台北午夜發出的對號快列車,折騰快五個小時,在天才濛濛亮的清晨四、五點到達台南,因為人生地不熟,五個人無處可去,只好在火車站前的廣場等。
好不容易熬到七點多,學長終於拉著板車來了,我們跟著他的身後走,從前站轉幾個彎就到了學校。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成功大學就在後火車站出口不遠處。
一九七四年,我這個台北人到了台南,才知道什麼叫做「城鄉差距」,當時最大的百貨公司只有三層樓,遠東百貨公司還是直到我大四才開幕。整個台南充斥各式各樣的夜市,每個夜市賣的小吃不盡相同,友愛街「沙卡里巴」的烤雞腿,是我每隔一段時間想家時,補償自己的珍饈。
台南另一個吸引我的地方,是到處可見的古蹟及廟宇。從赤崁樓、億載金城、武廟、五妃廟、開元寺、天后宮,到孔廟、竹溪寺⋯⋯等等,或香火鼎盛、或清幽僻靜,或雕樑畫棟、或古樸素雅,都是我在四年的就學期間,最好的私房景點及逃離塵囂的避風港。
成功大學是所歷史悠久,以「工學院」聞名的學校。建築古典優雅,樹木高大壯麗,榕園的那幾棵大榕樹及成功校區那一排高聳的檸檬桉,是我多年來最常被喚起的印象。
它創校於一九三一年,原名為「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一九四四年改稱「台南工業專門學校」,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數度易名,一九五六年改制為「台灣省立成功大學」,一九七一年改制為「國立成功大學」。
成大每個系都有個四合院,工學院的系所一長條排下來,從電機系、機械系、化工系......到最冷門的水利系。或許因為建系較晚,水利系不但排在最後,而且被塞在土木系旁的小角落裡,並沒有自己專屬的院子。
隨著學校經費愈來愈寬裕,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座座的四合院被一棟棟的摩登大樓取代。陪同我們度過每一個晨昏的成功校區運動場,也被一座美侖美奐的大圖書館占據。學校看似進步了,但人氣沒有了,過去迴盪在運動場上,各式球賽競技時響起的歡呼聲,也消失在偌大的校園裡。
三十多年來,我每次回成大,總會在昔日的籃球場旁駐足良久,緬懷昔日在球場奔馳的老友,依稀還能聽到歡笑及加油的聲音,最後總抱著若有所失的心情離開。
回想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讀水利系能做什麼,常被取笑將來要去蓋水溝、修馬桶,許多同學感到失落、徬徨,大一時拚命想轉學或轉系。我有位老同學張恭淦,正和後來的太太趙雅雯開始交往,雅雯的弟弟讀的是第一志願台大電機系,當她首次帶他回家見父母時,爸爸告訴女兒:「這個人從建中考到成功大學也就罷了,還讀了一個這麼冷門的系,鐵定不會有出息,不如早點散了。」就是這樣一個景況。

走筆至此,猛然憶起雅雯臥病多年,已在前年離開人世,恭淦不離不棄地在病榻前照顧到最後一刻。一對昔日人人稱羨的神仙美眷,就此天人永隔,令人不勝唏噓。
攤開當時水利系的師資名單,只有三位教授擁有博士學位,其中郭金棟教授還被借調去中興大學,教我們的老師多是博士班研究生兼講師,雖然他們之後在學術界都卓然有成,如黃煌煇老師後來擔任成大校長,歐善惠老師也成了成大副校長及南部某私立大學校長,蔡長泰老師更是台灣水利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但以水利系那時的師資,加上談不上先進的設備,在這樣艱困的狀況下,也作育出一批批英才。我們那個班五十位同學中,獲得博士學位在國內外大學任教的即超過十位,其他人也都在公私部門嶄露頭角。
事實上,水利系的「逃兵」中倒有不少名人。文學家白先勇先生的父親白崇禧將軍,當年希望他回大陸時可以整治長江、黃河,因此要求他從建中保送成大水利系,但他讀了一年發現興趣不合,毅然休學重考上台大外文系。物理學家丁肇中先生也一樣,滿懷壯志要回去大陸整治三峽,也在成大水利系讀了一年。還好人各有志,否則這世界將少一位大文學家及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後來我進入行政院服務,才發現前經濟部長張家祝先生、行政院長毛治國先生,都是從成大水利系轉到土木系的學長。
四十年前的成大,學生多數是南部人,我們這些台北人常被視為「異類」,處處顯得格格不入。台南的閩南語和台北的閩南語腔調非常不同,我常常被問是不是「外省人」? 如果是外省人為何會講台語? 更常有人問,我的台語講得不錯,但為何有個奇怪的口音等等。
當時正是嬉皮盛行時代,大學生風行蓄長髮,我也跟流行留了一頭披肩長髮,因為自然捲,滿頭翹翹蓬蓬。但當年的「違警罰法」(類似現今社會秩序維護法)賦予警察當街取締奇裝異服的權力,少年隊警員手持一把利剪,當街剪髮是常見的景象,以至於我每次回台北,走在街上還要躲躲閃閃。
成大的教官也因此對我非常感冒,常說:「這個傢伙一定是個壞蛋,頭髮留那麼長!」雖然我從不曠課,也自認是個用功的好學生,但大一的操行成績硬是被他打了七十九分。
事隔四十年,回頭看求學歷程,我只能讚嘆,這或許是「上天」的旨意,我註定要讀水利工程,把一生中最精華的歲月,貢獻給水利問題至今仍層出不窮的台灣。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記那些波光與映像:李鴻源人生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