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共鬥留下了怎樣的正面與負面遺產呢?
日本的68是否有思想,如果有,日本68思想是什麼?
內部私刑與肅清,暴力與殘殺與與外部恐怖襲擊導致新左翼運動全面敗退,以至於影響至今天的社運。依據日本警視廳調查,從1968—1975年之間,一共發生1776件內部暴力沖突,4848人受傷,44人被殺,另有3438人被捕。70年代21名「連合赤軍」在山區進行軍事訓練,以「肅清」名義殺害12名「同志」曝光之後,更是引起全社會的反感。
淺間山莊事件象徵日本學運與新左翼運動的休止符
1970年1月,赤軍派宣言建立世界同時革命根據地。同年3月,田宮等九人劫持「澱號」飛機,停留落在韓國金浦空港成功,他們到達北朝鮮後,試圖說服北朝鮮同意他們去古巴接受軍事訓練後回到日本革命,但是眾所周知。他們不得不留在北朝鮮,他們開辟了「日本革命村」,直到近年被控告參與北朝鮮綁架日本人事件。
劫機事件後,赤軍派在國內無法開展活動。1970年1月—7月,249人被逮捕。幾乎失去所有的幹部,內部動搖,組織陷入危機。
1971年重信房子等人赴巴勒斯坦。而後造成特拉維夫機場亂射事件。
1971年美國支援南越進攻解放戰線基地老撾。周恩來飛河內,宣稱如果美國再進行挑釁,中國將不惜性命支持北越與老撾。這條消息極大地鼓舞了日本左翼陣營。革命左派(京濱安保共鬥)與赤軍派聯手,成立連合赤軍。
1972年發生連合赤軍事件。在群馬縣的山裡,武裝集團在秘密基地私設刑堂,用殘酷的手段殺害12名「革命同志」,他們在逃亡的路上,占據淺間山莊。扣押人質,與警方展開槍戰。兩名員警殉職,一名民間人死亡,他們卻毫髮無傷。更為重要的是連合赤軍在革命與正義的口號下內部殘殺的血腥暴力極大震撼日本社會,至今留下後遺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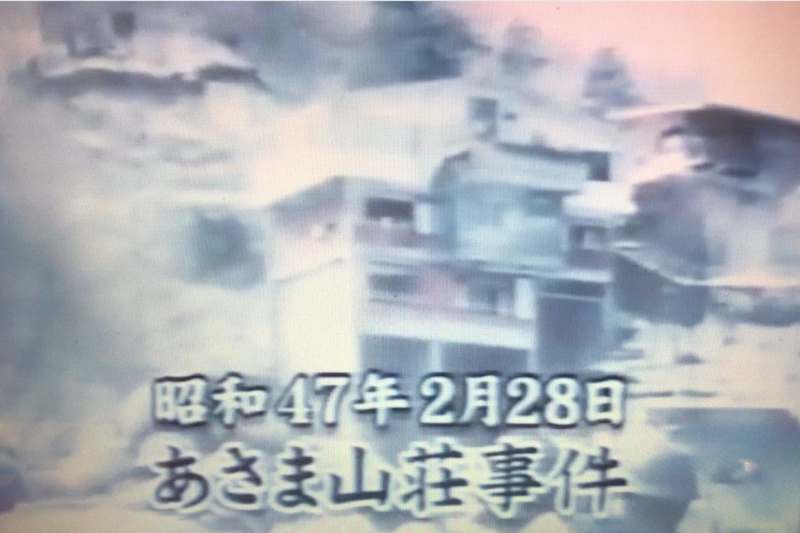
曾經是東京產業大學學生的阪口宏紀錄了自己的心路歷程,從大學退學後苦心研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毛澤東的中國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就是在山溝溝的革命基地,還在讀《毛主席語錄》,他紀錄了尼克森與毛澤東握手時自己的痛苦與思考,以及淺間山莊時吉野的母親喊話:
「兒子,時代已經變了,毛澤東先生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這一細節。
三兄弟一起參加連合赤軍的加藤墩教回憶:父親是一個小地主出身的有進取心的小學教師。非常注重三兄弟的功課。我們三兄弟首先極為反感父親的生命方式,進而對充滿物欲的經濟成長的日本社會反感。反越戰是我們兄弟感情的樞紐,當時大部分年輕人共有這個樞紐。喚醒惡年輕人的加害意識。罪惡感擁有絕對價值觀的共產主義與眼前的現實存在真是南轅北撤的對照。我們想成為共產主義者,試圖在那裡找到我們存在的價值」。「我三兄弟連架都不吵,怎麼會去參加暴力革命呢。漫畫七色鐵臂阿童木、鞍馬天狗等「正義少年」是我們產生全能感。
1974年,武裝革命團體「東亞反日武裝抗日陣線」用炸彈襲擊三菱重工(日本最大的軍需企業)總公司大樓,因為「日本帝國的勞動者。市民是壓迫殖民地民眾的帝國主義者、侵略者」。參加者後來回憶,作為侵略亞洲的日帝子孫,否定醜惡的自我存在只為贖罪。
連合赤軍私刑暴力事件以及淺間山莊事件事件後,川本三郎說,淺間山莊事件。使得我夢想的東西,化作泥濘崩潰。我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那個時代的象徵,說起來就是在下雨,路障底下全是淹沒了水。
他引用詩人佐佐木幹郎詩歌: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歌手加藤登紀子說,對我來說,六十年代意味著敗北。從1968年起,我成為了局外人。
更有人認為1968年全共鬥全國大會的在東大安田講堂召開時,意味者內鬥開始學運衰敗跡象。
岡林信康於1968年春從一個土木工人轉為民謠歌手。以歌為連帶發展運動。
1970年6月,安保條約自動延長,美軍逐漸從越南撤兵,日本經濟成長步入軌道,貧富懸殊變小,邁向「一億中流」社會。自民黨在1969年選舉中獲得大勝。
至今為止,企圖改變日本社會的行動大多以失敗告終。
但田中有理認為,失敗的只是組織或者政治意義上的,作為自我解放與自我否定,永無敗北。
給予「六八」一個單一的「正確評價」是困難的,將任何事項只用一個公分母總結評價會掉入陷阱。

1994年《全共鬥白皮書》出版。對以下問題做了問卷調查,日大全共鬥領袖秋田明大回答:「如果再回到那個時代,還大幹一場嗎」。不幹,傻瓜。
運動中有得失嗎?——出了臭名。
現在的收入?——一年兩百萬。
是否還讓你的孩子參加學運?——反對。
現在的感覺?——身心疲勞。
「我們一無所有,難道就不能進行鬥爭了嗎?」
五十年後仍未解讀「六八」,因為「六八」仍在運動中,與其說作為歷史,毋寧說作為「現在」,即當下。68之後,許多人向右轉向,也有人向左轉向。但毫無疑問,今日日本社會的撕裂或者說多元化,與68分不開,而且,進步知識人對誤導的責任至今語焉不詳,對今日中日關係,中日問題的認識都有影響。
日本的新左翼運動對政治體制的影響相當有限。沒有像歐洲一樣反映到政治層面上去。
日本公民社會對直接行動感到厭惡。
安藤丈將認為,六十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並不是一場以實現特定政策為目標的政治運動,而是一個「權力」與「自我變革」在「日常性」這個過程中的相互作用。發現「日常性的自我變革「這個問題,正是日本六十年代社運的最大功績。七十年代後的日本公民運動包括:環保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權益運動、援助開發中國家、反核運動等,這些運動都有發省自己在物質上的充裕生活。對弱勢族群的痛苦思考的模式。安藤認為,這一共通的思考模式,與六十年代「日常性的自我變革」思想一脈相同,承上啟下。
1,從對戰後民主主義的肯定到否定,2,對近代合理主義的肯定到否定。3,從被害者意識到加害者意識的轉換。進入七十年代後,源於第三點的加害者意識,七十年代後新左翼運動開始關注戰爭責任、歧視部落、在日朝鮮人、沖繩問題、女性問題,弱勢群體問題公害問題、有機農業耕種等國內問題,以及追究戰爭責任問題。可以說,全共鬥運動留下的遺產也包括公民運動的起源。自主學習運動的起源。七十年代以後「寺小屋」與「自主講座」如雨後春筍。實踐「自我變革」,建構自我主體性的一環。安藤丈將《新左翼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十年代的思想之路》(林彥瑜譯)書中刻意選用「ニューレフト」(newleft)一詞來表達,不使用「新左翼」這個傳統詞語。目的在於回避數幾十年來在日本公共論述中負載的負面含義,如黨派、宗派主義、意識形態教條以及暴力革命等。試圖將「新左翼」在大眾想像中的政治性與意識形態性格以清除與降低。他認為這一場運動史戰後嬰兒潮青年時代試圖進行「自我變革」,並將自我變革連接到改變社會的倫理性運動。這種自我變革,要求改造社會要從改造自我做起,因此要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實踐開始,安藤認為,日大、東大的全共鬥鬥爭,以及反對成田機場興建的三裡塚,本質上都是這種青年試圖自我變革的象徵。其次,安藤認為,引發學生自我變革反抗的,是日本高度成長的日本國家與資本主義對日本人消費性與政治馴服的校規。新左運動的核心是:「日常性的自我變革」,即便它用政治語言「帝大解體」來表達。「日常性自我變革」的倫理基礎是,一旦知道了世界上有不公不義的事情,我們就不能假裝它沒有發生。
他們現在在哪裡?
他們不像德國學運人一樣從政(比如歐洲綠黨)多成為學者,一般就業
山本隆義:原東大全共鬥會議代表。學運象徵性領袖。1969年9月在全國全共鬥連合結成大會上被捕。
他本來是日本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新星。運動後離開大學,成為駿台預備校物理學教師。其科學史著作獲得每日出版文化獎等多個出版獎。
從日本2011年複合震災前就一直反對建設原子能發電站。
今井澄:參加60年安保鬥爭,反對大學管理法。東大全共鬥時期是醫學部學生。安田講堂防衛隊隊長,被關進東京拘留所一年。第三次復學之後考上醫生執照,為地域醫療做貢獻。並當選過參議員,反對國旗、國歌法案。2000年去世。
秋田明大:日大全共鬥會議領袖。學運象徵性人物。現在在家鄉廣島附近開了一家汽車修理工廠,年收入低,對他來說,迫切的是「生活」。
島泰三:東大理工部學生,參加安田講堂龍城判刑兩年。現在野生生物研究者。出版《安田講堂1968—1969》等。
藤本敏夫與加藤登紀子:
藤本敏夫是同志社大學文學部學生。1967年參加羽田鬥爭,並以此為契機,活動重心轉移到明治大學,1968年擔任反帝全學連委員長。1968年參加國際反戰日防衛廳前抗議活動被逮捕。1969年因不滿學運派閥內鬥,脫離學運。1972年因「公務執行妨礙罪、兇器準備罪」被判刑三年八個月。
1972年與加藤登紀子獄中結婚。加藤自己作詞作曲的歌曲《一個人睡覺時的搖籃曲》獲得1969年度唱片大獎。監獄中得知連合赤軍內部殺人事件而絕望。1974年以後實踐農業理想,普及有機農業。他在自傳中回憶1968說「象徵1968年的六十年代後半一系列活動是時代本身理不僅的思想的噴發,近代社會的深呼吸」。
清水幾太郎:原為自由主義者,知識界「安保批判會」核心,全學連的理論代言人。清水已經從自由主義者「轉向」為保守主義者。1980年在右翼政論刊物《諸君》上發表《核的選擇—日本,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
新島淳良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為文革與日本學生運動相互關聯的理論考察中,在日本公共論壇中登場次數多、有影響力和受人注目的理論家。新島甚至試圖將文革的公社的概念和體制移植到日本,掀起日本的文革。
他的文革理論直接影響著學潮運動和新左翼運動。新島的政治烏托邦是「公社國家論」,林彪之死,淺間山莊事件之後,日本左翼革命派失去民心和道德的制高點,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
新島淳良:一個被文革革了命的學者
一九七三年,新島出於思想的潔癖,追求知識人當吹鼓手的自我責任。主動向早稻田大學出辭職。一個叫「山岸會」的共產式供給體制共同體出現在新島面前。他將所藏書籍全部義賣,捐獻給他心中的毛理想公社。自願「下放」到位於三重縣伊賀町山岸會,掀起山岸主義幸福學園運動。在勞動中,新島不斷反省,自我批評,認識到自我想像的毛主義公社的烏托邦與現實的出入,坦白和內疚自己目睹紅衛兵的暴力造反,相互殘殺,警覺到烏托邦的暗黑一面,但還鼓吹文革的積極意義,誤導輿論。新島向自己的信仰舉起鋒利的手術。新島在山岸會又經歷了退出和再加入的反復歷程,終他認為山岸會「沒有變質為極權主義」。二〇〇二年去世後葬於山岸會共同公墓。
毛的烏托邦復活了日本和西方左翼知識份子的政治期待和訴求。只是他們經歷的是精神痛苦,而中國人卻經歷了幾千萬無辜生命的痛失和對文化理想,道義尊嚴的淪陷。林彪事件以後,文革禮贊派幾乎都將自己置於受害者的立場,都輕而易舉地摒棄了自己的言論責任,他們忘記了那些高分貝語言殺人的潛威力。海因裡希伯說:「殺人與否,關鍵在於良心,在於人們是否把語言引導到可以殺人的地步。」那些負責引導和詮釋語言的「論者、公知」們,那些手持麥克風,壟斷話語霸權,挾持語言,給語言注射嗎啡的人,使得語言產生毒癮的人,有多少進行過自我解剖和坦承責任呢?
新島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學者,他耿直得透明,實誠得不會耍花招,不會變換一件馬甲,他的生存智慧似乎不高,處世策略也不精明,好像也不熟諳「學術和理論」的遊戲規則,如果他繼續保留名牌大學教授的位置,仍然可以獨佔資源的優勢繼續在「學術」空間裡自娛自樂,甚至拉幫結派,培養門閥,陶醉於無聊的學術應酬和吹捧,文革後照樣可以在酒飽飯足後進行「中日友好」,從利益共同體中分得一杯「共同專案、學術交流」之殘羹,然後對中國的痛苦做做俯臥撐,玩玩躲貓貓之類的遊戲。

然而新島固守了內心的價值選擇,他理想的挫折和自省,他行動的誠懇和執著,可視為日本知識人戰後思想譜系的一個重要座標。他自願把自己置身於固有的主流秩序之外,並暴露自己的笨拙和傷痛,以「圈外人」、「邊緣人」的身份發聲並實踐著。
晚年的新島曾自諷為是「被文革革了命的人」。退出公共論壇後,先後創辦了三份個人小刊:《吶喊》、《彷徨》、《墳》。分別代表他晚年的三種心態。據訪問過新島的遺孀新島裡子女史的蔣同學說,裡子女史得知其夫的論著將被譯成中文,十分欣慰。「他(新島)生前太熱愛新中國和毛澤東了,以致被這種熱愛沖昏了頭腦。作為學者,他也許失敗了,但是作為一位誠摯的日本人,他義無反顧,無怨無悔。希望中文讀者能夠透過他的文字來瞭解一位元真實的新島淳良。」
新島精神坦誠,但他的毛思想研究,並不符合俺的思路,也不合時宜,當然更不代表俺的表述。他山之石,倒是給當代中日兩國留下了一份精神遺產,使我們得以拓寬視野,更加寬容地進行學術研究。新島作為知識人的獨立之信念,自由之精神,責任之清算,也同樣拷問我們的天良和底線。
日本還會發生學運嗎?
荷宮和子:學運已經滅絕。
不婚,不育。被拋入「下流社會」。對全共鬥的「正義」的質疑。不相信「公眾」的力量能改變什麼。運動暴力造成日本社會心理的集體創傷。
*作者現任教於日本神戶大學。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日語譯有《從天安門到08憲章》、《殺劫》等,漢語有《這條河,流過誰的前生與後世》《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合譯)。本文為作者應邀於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的演講完整版(之四)。授權轉載。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