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隆冬,這一天卻是個陽光普照的好天氣,整個城市早已熱絡活動了起來。在防波堤的底端,水天連成一線。伊瓦爾沒去注意這些,他只顧著賣力騎著腳踏車在這港口的唯一大道上一路前進,他把殘障的那隻腿放在踏板上,一動不動,另一隻腿則使勁地踏著車子前進,行走在這夜裡留下的充滿濕氣的濕漉漉道路上。他穩穩坐在座墊上,頭抬都不抬,一路避開舊街車的鐵軌,他有時會緊握車把猛然晃一下,讓前面穿梭如織的汽車通過。他有時會用手肘去碰一下綁在腰部的布袋,費蘭德為他準備的午餐就放在那裡,他一想到布袋裡的午餐,就覺得有些苦澀,兩片大麵包中間夾的不是他所喜歡的西班牙歐姆蛋,或是油煎的牛排,而是一小塊乳酪。
他從未覺得到工廠去的道路像今天這麼漫長,他老了,已經四十歲了,雖然仍堅廷得像葡萄藤的新枝,肌肉的活力可沒那麼靈光了。有時候他讀體育報導,他們稱三十歲的運動員為老將,他就聳聳肩。「如果這叫做老將,」他對費蘭德說:「我就是死人了。」其實,那些記者這樣寫並不是沒道理,一個人到了三十歲,氣不再豐盈,只是還看不出來而已,到了四十歲,即使還未躺下來,不,還未,但也是要提前做準備了。許久以來,每次他要前往城市另一頭製桶廠上工經過海邊時,再也沒興致看大海,不正說明了這個現象嗎?他二十歲時,單單看著大海是不夠的,大海總會帶給他一個愉快的週末,即使一條腿瘸了,他還是非常熱衷於游泳,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娶了費蘭德,生了一個小男孩,為了生活,他就利用星期六空閒時間到製桶廠加班工作,星期日就打零工幫人修理桶子,慢慢地,年輕時候曾讓他心滿意足的瘋狂習慣就跟著消失了,清澈深邃的海水,炙熱的陽光,年輕女孩,洋溢著青春火力的身體,這是這地區真正的快樂泉源,如今都與他絕緣了,隨著青春的消逝,這些快樂都跟著不見了。伊瓦爾依舊喜歡大海,但只有天色將晚,海灣的海水變得黯淡之時,在這溫暖的時刻裡,在一天工作之後,他坐在家裡的平台上,穿著費蘭德為他燙好的乾淨襯衫,喝著有氣泡的茴香酒。不久夜色降臨,天空一片寧靜,鄰居用很細微的聲音和伊瓦爾講話。他分不清楚他是否快樂,或是很想掉眼淚,但至少在此時此刻他覺得很滿足,他靜靜地等待,只是不知道在等什麼。
早上的時候,他必須回去工作,路上他再也不愛看大海,大海卻總是在那裡,忠心耿耿等著他,他只有在晚上回家時才會看它。這天早上,他騎著腳踏車,低著頭,比平常還沉重,心頭也一樣沉重。前一天晚上開完會議後回來時,他宣稱大家必須回去工作。「這麼說,」費蘭德很高興地說道:「老闆同意給你們加工資了?」老闆並未給他們加工資,罷工失敗了,大家並沒有很認真去罷工,意氣用事罷了,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公會有理由不好好跟眾人配合,只有十五個工人左右發動罷工,這成不了氣候,公會曾考慮到其他經營不善的製桶業,他們不配合,這不能責怪他們,製桶業最近受到造船和油罐車的威脅,很不景氣,人們越來越不想做桶子,葡萄酒的酒桶也不想做,大家都修一修現有的大桶子,將就著用。老闆們看出他們的生意必須妥協,另一方面又想維持他們固有的利潤,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凍結工人的工資,即使生活物價一直在上漲。當製桶業維持不下去時,製桶工人怎麼辦呢?他們做了一輩子桶子,你無法叫他們轉行做別的,這相當困難,你總不可能要他們改行一切從頭做起。一個熟練的木桶工匠,他能夠把一塊平板的木塊弄彎,再用火慢慢烘烤成圓圈,然後用鐵圈加以框住,像煉金術一般,不必動用到棕毛或廢麻,就能做出一個很美觀又很管用的桶子,這樣的技藝很稀罕,而伊瓦爾對此相當熟練,他很以此為傲。要轉業並沒什麼,但是要他放棄已經熟悉的技藝,這可不容易。一個美好的職業,卻無從發揮所長,人被框在那裡,無所事事,不如辭掉算了,但是要辭掉工作,談何容易。如今要把嘴巴閉起來,不去好好討論工資問題,這也是很困難的。每天早上帶著越來越疲憊的步伐,循著相同的路徑去上工,只是為了等到週末時老闆給你一點工資,然而,這點錢已經越來越不夠用了。
他們開始憤怒了,有兩三個人還在遲疑,但是在第一次和老闆討論過工資問題之後,他們也開始憤怒了。老闆話說得很冷淡很直接,要就接受,不要就拉倒,這話說得有夠直接。「他在想什麼!」埃斯坡吉托說道:「要我們把褲子都脫了?」其實,老闆並不是個壞人,他從父親那裡繼承這個事業,從小就在工廠裡長大,多年來差不多認識了工廠裡每一個工人,他有時會邀請他們在廠裡吃點心,烤沙丁魚或豬血腸,還讓大家喝酒助興,他真的是個不錯的人。每當過年時,他會送每個工人五瓶好酒,每逢工人之中有人生病、婚嫁或受洗,他都會包禮金致贈。他女兒出生時,每個工人都分到了杏仁糖,有兩三次,他還邀請伊瓦爾到他海邊的私人領地打獵。毫無疑問,他很愛他的工人,他也常回想他的父親是學徒出身,但他從來不會想要去工人家裡,他不了解他們,他只想到他自己,因為他只認識他自己,現在他才會說,要就接受,不要就拉倒。這回輪到他耍脾氣了,而他竟然可以真的這樣幹了。
他們強行訴諸工會罷工,讓工廠關了門。「你們不必麻煩弄罷工糾察隊來監視,」老闆這樣說道:「工廠不開工,我樂得省錢哩。」這不是真的,但這樣說於事無補,他當著大家的面說,他給他們工作是可憐他們,是施捨他們,這下子把埃斯坡吉托惹火了,他憤憤地說老闆簡直不是人,其他幾個人也開始熱血沸騰,怒不可遏,有人把他們拉開了。這時其他工人也軟化了,大家決議罷工二十天,這下子家裡的女人們開始憂愁了,有的甚至變得很沮喪,最後工會出面協議停止罷工,仲裁結果,以加班幾個鐘頭時間來彌補罷工損失,大家很心不甘情不願回去工作,同時放話,這不是結束,大家還會再見。今天早上,失敗的沉重感覺無以復加,讓他感到疲憊無力,乳酪取代了牛肉,不要再存有任何幻想了。陽光普照,大海再也不能承諾什麼。伊瓦爾單腳踏著腳踏車前進,每踏一下,他就覺得變老了一點,他此刻不能想到工廠、同事以及老闆,他一想到等一下要和老闆見面,心裡就越發感到沉重。費蘭德一直在擔憂著:「你們要跟他說什麼?」「什麼都不說。」伊瓦爾騎著腳踏車,一面搖搖頭,他咬緊牙齒,棕色的臉上已經有皺紋,臉雖繃著,但不難看。「大家回去工作,就這樣。」現在,他踩著腳踏車前進,牙齒仍咬著,臉上流露著一股乾癟而哀傷的怒氣,和天空互相輝映著。
他離開了大道和大海,轉入舊西班牙區的濕漉漉街道,這幾條街道通向一個堆放廢鐵的倉庫和修車廠的區域,他的工廠就矗立在那中間,看起來就像個大廠棚,牆只砌到一半,往上就是透明的玻璃,一直往上延伸到波浪形的鐵皮屋頂。這個工廠面向一座舊的製桶坊,有一個四周圍圍著小庭院的大庭院,當工廠生意興旺時,這個大的庭院就廢棄不用了,如今已變成堆積廢棄機械和舊桶子的地方,在大庭院的另一邊,由一條堆滿舊瓦片的小路隔開,那是老闆的花園,花園的另一頭,就是老闆的住家了。房子很大很醜,但由於外面的樓梯布滿五葉地錦和稀疏的忍冬花草,整個看起來還是滿可愛的。
伊瓦爾第一眼立即看到工廠的幾扇門關閉著,一群工人靜靜地站立在這些門的前面。自從他到這裡工作以來,這是第一次他來上工時看到工廠的門是緊緊關閉著的,老闆似乎在藉此表示他占了上風。伊瓦爾往左邊走過去,把腳踏車停放在從庫房延伸出來的棚子底下,然後走向大門,他從遠處就看到和他一起工作的埃斯坡吉托,這是一個有著棕色皮膚,全身毛茸茸的高大傢伙,還有工會的代表馬庫,長著一個像唱假聲男高音的腦袋瓜,另外還有薩伊德,工廠裡唯一的阿拉伯人,其他工人靜靜站在一旁,看著他走過來,但就在他要加入他們之時,大家突然轉身走向大門,大門剛剛打開了,工頭巴列斯特正背對著他們,把沉重的大門往一旁的盡頭慢慢推了過去。
巴列斯特是這裡年紀最大的一位,他一直不贊成罷工,但自從埃斯坡吉托說他是在為老闆的利益服務之後,他就噤聲不說話了。現在他穿著深藍色毛衣,赤著腳,大剌剌站在門邊(他是薩依德之外在工廠裡工作時唯一赤腳的一個人),看著大家一個一個進來,他那黝黑臉龐上的兩顆淡色眼珠子顯得特別清澈,那濃密而下垂的八字鬍蓋著的嘴巴顯得有些哀傷。大家默默魚貫進入廠房,因挫敗而感到屈辱,但隨著走進廠房,大家似乎也就不去理會這股沉默了,更不去注意巴列斯特的存在,大家知道他只是執行命令要大家以這種方式回來工作,大家看得出他臉上苦澀懊惱的表情,很清楚他內心的感受。伊瓦爾一直瞪著他看,巴列斯特向來很喜歡他,這時只是跟他點一下頭,並沒說什麼。
現在,他們都來到進入大門後面右手邊的小更衣間,有一些用白色木板隔開的置衣箱打開著,每一個置衣箱旁邊各掛著一個上鎖的小櫃子,從進門第一個置物箱一直到廠房旁的牆壁已經改建為洗澡間,地上還闢出一條小溝當作排水之用。在廠房的中央,每個工作據點,堆放著一些已經快要完工的葡萄酒桶,只差尚未框上圓框而已,同時在等著用火烘烤,在桶子厚厚的底盤上面,要挖出一條長縫(有的則鑿出一個圓盤,然後再加以拋光),最後用旺火燒烤。在大門入口的左手邊,沿著牆壁一路過去,則是一整排的工作檯,在這些工作檯前面,堆放著一堆等著刨平的木板塊,在右手邊靠著牆壁的地方,離更衣間不遠,擺著兩座大型電鋸,已上了油,堅挺銳利,靜默無聲,閃閃發亮。
許久以來,這個工作廠房對這一小撮工人來講已經顯得太大,在大炙熱天氣下倒還好,冬天時就顯得不那麼舒適了。可是在今天看來,在這麼大的空間當中,工作固定在那裡,角落到處零零散散堆放著桶子,頭頂上一個大圈圈推放著一堆豎著的木板,看起來就像一些綻放的粗糙的木板花擺在那裡,木板凳上、工具箱上以及機器上,到處沾滿鋸屑,整個工作場看起來就像是廢棄了一般。他們進來之後四處張望,現在大家已經穿上舊工作服,褪了色和充滿補丁的褲子,卻還在遲疑不動,巴列斯特看著大家,「怎樣,」他說道:「咱們可以動工了吧?」大家一個一個走向自己的工作崗位,半句話不吭。巴列斯特走到每個崗位上,簡單提醒每個人,要就動工,要不然不要做算了。沒有人回應,這時傳來一聲錘子敲在桶子中間框著鐵圈部位的聲音,刨子也開始發出刨平木頭上不平地方的聲音,埃斯坡吉托啟動電鋸,發出鋸齒在鋸木頭的摩擦響聲,薩伊德依照吩咐抱著一堆木板跑來跑去,或是捧碎木屑去生火,讓別的人在那上面烘烤桶子,讓框鐵圈部位鼓起來。沒人叫他時,他就拿著鐵錘沿著工作檯用力敲打生鏽的大圈圈。碎木屑燃燒的香味開始瀰漫整個工作廠房,伊瓦爾刨平並修整埃斯坡吉托已經裁剪好的木板,這時聞到了燃燒木屑的香味,內心緊縮了一下。每個人靜靜地工作著,一種熱絡,一種生命的再生氣氛開始慢慢充塞整個廠房,一道清新的太陽光線穿過那塊大玻璃,滲透入廠房各個角落,連空氣都閃爍著一種金色光芒,襯托出一層藍色的煙霧,伊瓦爾彷彿聽到旁邊有昆蟲在鳴叫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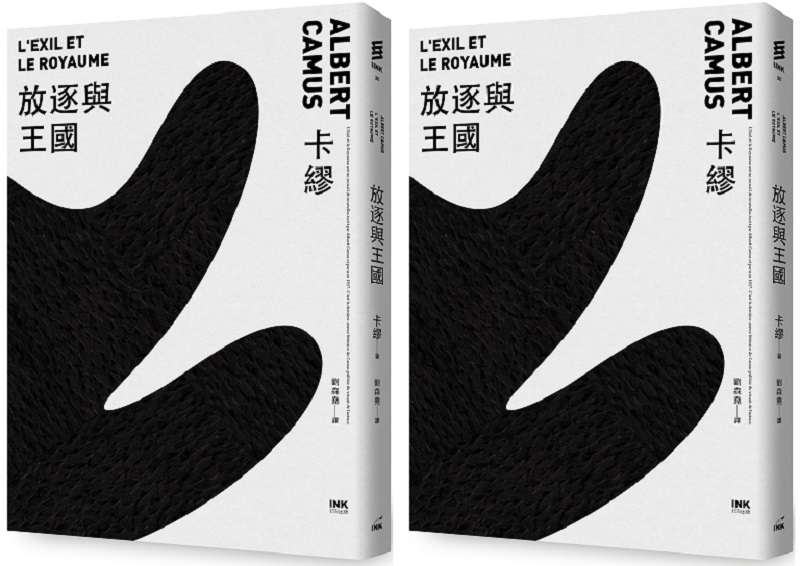
*作者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本文選自作者生前最後一部作品,短篇小說集《放逐與王國》(劉森堯譯,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