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學上,對於「衍生性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有所謂「毒樹果實理論」(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該理論的邏輯是:如果證據的來源(樹)受到汙染,那麼任何從它衍生獲得的證據(果實)也會受到汙染。因此,這樣衍生出來的證據,在訴訟中不具備證據能力。 同樣的邏輯,當我們在追求轉型正義,尋找歷史真相時,更要注意是否採擷到了「毒樹果實」?以免誤導了轉型正義。
近年來,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李中志教授,從故紙堆中,翻出了1947年3月29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一篇題為「Taiwan Island’s Blood Bath」的報導。
這篇七十幾年前的報導,是由約翰・威廉・鮑威爾 (John William Powell)執筆的。他曾於 228 該年的3月19日抵台、27日離去,在台灣待了九天。這篇報導據稱是「英文世界」第一篇對228事件的報導。該報導經李教授翻譯成題為「台灣的血浴」。宣稱發現了若干所謂前所未聞的「228血腥暴行」,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與震撼。
美國記者筆下的「台灣血浴」
鮑威爾在他的報導中,對於國府軍隊的鎮壓暴行,有許多血腥的情節描述:
「一位外籍人士看到一位騎腳踏車的男孩被攔下,顯然因為他停下來舉起雙手的速度不夠快而惹怒了憲兵,他們命他伸出雙手,然後用刺刀砍下雙手再砍人。」
「發生在台北基隆之間的一處村落,20位年輕人被屠殺。在他們被刺刀刺死前,先被閹割、去耳、削鼻,之後屍體被丟入溪流,棄置數日。」
「在台灣南端的打狗,數千人從監獄被拖出來,雙手以鐵絲捆綁,中間絞緊讓鐵絲切入手腕的肉裡。」
「軍警快速巡邏隊,以架設機關槍的卡車在市區疾駛,向群眾掃射。檢驗槍傷與散落的彈殼顯示,軍隊使用了達姆彈,以造成恐怖的傷口,往往致命。」
情節有悖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由於威廉.鮑威爾是一位美國人,他所代表的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又是當時在中國發行的英文週報,不但是在華西方人士閱讀的主要英文媒體,同時也是當時的西方媒體報導中國新聞的主要消息來源。
因此,後來若干西方媒體對「228事件」的報導,基本上,都是以「密勒氏評論報」的報導為藍本改寫的。以致於威廉.鮑威爾這篇有關國府鎮壓228血腥暴行的報導,產生了「一槌定音」的效果。當然,這也是這篇報導會被翻出來,並對「後228世代」的我們,產生了駭人聽聞的震撼效果。
但是,任何報導最起碼得要經得起「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的檢驗。所謂經驗法則係指吾人其於日常生活經驗所得之定則,並非個人主觀上的推測而言。而所謂「論理法則」即邏輯法則,亦即推論是否合於邏輯。
令人不解的是,上述諸多恐怖又不可思議的「目擊故事」,例如:「20位年輕人被屠殺。在他們被刺刀刺死前,先被閹割、去耳、削鼻」,以及在高雄「數千人從監獄被拖出來,雙手以鐵絲捆綁」鮑威爾自稱是他「從可靠的外籍目擊者那裡取得的」。
但是,經過這幾十年來,台灣各公民團體,甚至學術機構對228事件當事人所作的口述歷史或訪談資料中,為什麼都沒有台籍的目擊證人呢?這就不免有悖「論理法則」了!
其次,從「經驗法則」來看,當過兵的人都知道,「刺刀」是用在「刺槍術」中「刺」的功能。拿「刺刀」削甘蔗都很困難,更遑論「用刺刀砍下雙手」。顯然這段描述,違背了我們大家的「經驗法則」。
鮑威爾228報導的「消息來源」
那麼鮑威爾所報導的血腥故事,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根據鮑威爾自述,他是在3月19日抵達台北的 。但是,228事件發生到3月15日,全台已大致恢復平靜了。
換言之,他所能採訪到的,不是現場目擊的「新聞」而是經過二手或三手傳播的「傳聞」。因此,在他的報導中,對於引發事件的「女主角」林江邁的情況就有明顯的錯誤。
鮑威爾當報導:林江邁被「警察以槍托重擊死亡」。但事實上,林江邁當時僅受輕傷,她後來一直活到民國五十八年才因罹患肝硬化而死亡。
其次,在鮑威爾的通篇報導中,他一再聲稱引述自「外籍人士」的目擊。但是,他卻沒有交代清楚,所謂的「外籍人士」究竟是什麼人?
事實上,228當時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不久,在台灣的「外籍人士」為數不多。此,鮑威爾來台採訪,最有可能接觸的「外籍人士」,當屬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官員。根據文獻記載,美國當時駐台領事館,只有三位美籍官員。領事布雷克Ralph J. Blake,,領事葛超智George Kerr,聞處主任卡竇Robert J. Catto。
孫科1948年2月來台訪問時,曾在演說中指控「美國駐台領事館的一位新聞官員」,「利用美國記者不諳地方語言,從中歪曲事實⋯⋯」顯然孫科暗指的「新聞官員」是卡竇。但是,我們卻可在副領事葛超智的著作《被背叛的福爾摩沙》Formosa Betrayed 一書中,卻可發現若干與鮑威爾的報導,高度雷同的故事。其中第一手的線索是「達姆彈」的故事。
鮑威爾報導情節與葛超智雷同
根據「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第十四章標題為「三月屠殺」中,葛超智宣稱他曾親自處理了一起有關「達姆彈」的投訴:
「3月2日在領事館⋯⋯我們的工作被一個台籍醫師的來到所打斷。這位醫師跟幾個朋友帶來一顆軟鼻子彈,他要求領事館向有關當局提出抗議,理由是:國際協定上,明文禁止使用軟鼻子彈。」
葛超智所說的「軟鼻子彈」就是所謂的「達姆彈」Dumdum bullets。由於達姆彈具有變形擴散的特性,會造成嚴重的傷口,而引發人道爭議,因此在1899年海牙公約明文禁止在國與國交戰時使用這型彈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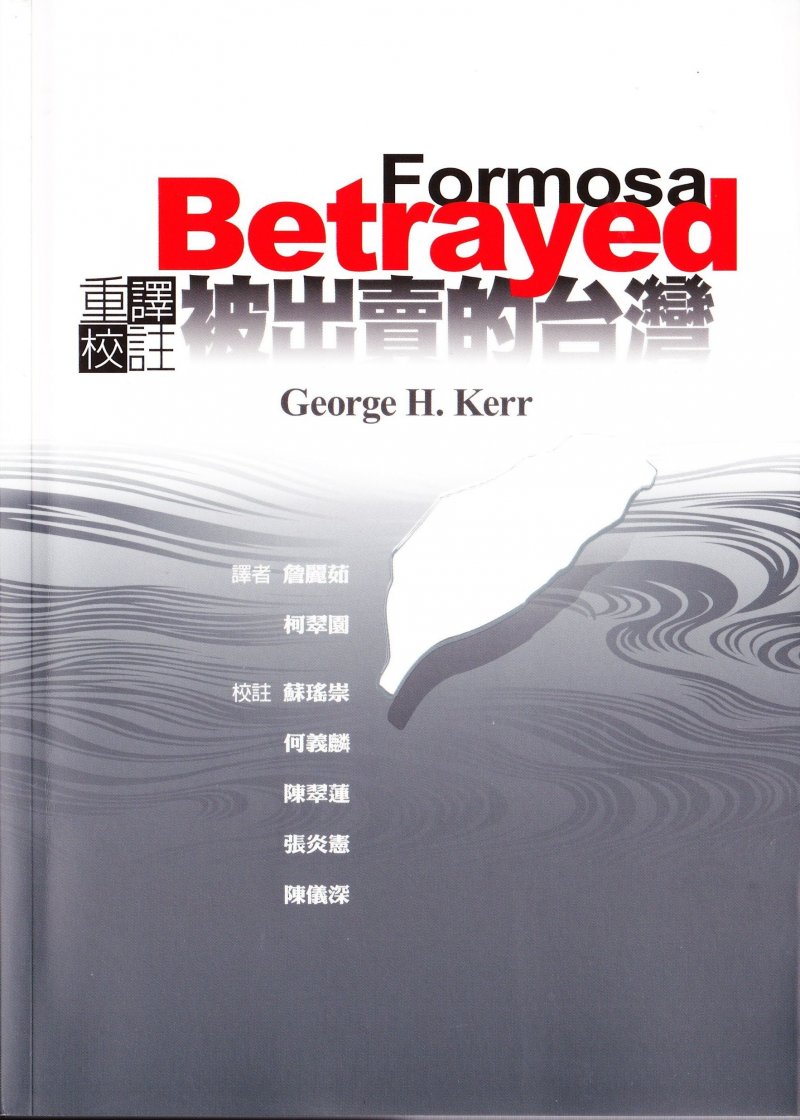
但是,葛超智這個達姆彈的故事,卻又有點超乎「經驗法則」。以筆者17年的職業軍人生涯,我從不曾在課堂或野外聽教官介紹過這種子彈。即便把這種子彈擺在眼前,我也無法辨識這種不曾見過的特種子彈。
那麼葛超智所說的那位「台籍醫生」究竟是何來歷?他又是如何辨識那棵「軟鼻子彈」就是「達姆彈」呢?他又何以知道使用這種子彈是違反國際公約的呢?當然是值得懷疑的。但是,這個「達姆彈」的故事卻繪聲繪影的寫進了鮑威爾的報導。然而,從這個線索中,卻也顯示出鮑威爾的報導極可能源自葛超智。
譬如:關於「20位年輕人被屠殺」的故事,葛超智的書中是這麼說的:
「一個外國人在台北東區的路旁,計數到三十多具,身穿學生制服的年輕屍體,他們的耳鼻被切除,還有很多被閹割,有兩個學生在靠近我前門的地方被砍頭。」
顯然兩人描寫的血腥情節雷同,但是發生的地點和受害人數則有所不同。
又譬如:鮑威爾所敘:男孩被刺刀「砍下雙手」的故事,在葛超智的版本中則是這麼說的:
「一個外國人,看到一個少年在街上飛快地騎著自行車⋯⋯他被人從自行車上打下來,又被強迫伸出手來加以砍打,然後國民黨軍隊把自行車劫持而去,任那孩子無助地在街上流血。」
顯然與鮑威爾的報導,情節雷同,血腥的程度則有所不同。
根據文獻記載,葛超智是在三月十七日奉美國駐南京大使館之召離台的,而鮑威爾則是十九日入台的;顯然他倆錯身而過。
但是,怎麼會有這些相似的情節,出現在彼此相隔十幾年的著作中呢?尤其,在評估 228的死亡人數上,當時有許多不同的數據,唯有葛超智和鮑威爾一致評估為「5000人」。
這會不會是葛超智早已備有一份關於228的「參考資料」,隨時可以發送給西方媒體使用的呢?而讓後到的鮑威爾有了報導的依據?
葛超智的228角色備受爭議
葛超智在228事件爆發時,是美國駐台的「副領事」vice consul。但是,長期以來卻被台獨人士尊為「台獨教父」。因為,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就曾在日治時期的台北,教了三年英文。228事件中,好幾位檯面人物都是他曾教過的學生。

二戰期間,他是美國海軍的情報員,曾參與攻台計畫的「民事」準備工作。大戰結束後,他也是極少數最早抵台的美國官員之一。後來,更成為剛成立的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副領事。
但是,葛超智這位賓州長老教會的牧師之子,最引人側目的是,他附和當時美國軍方部分人士的意見,認為:日本的降伏是美軍的功勞。因此,台灣應是美軍的「戰利品」之一,理應以美國的戰略利益,來決定台灣的歸屬。
他們操作美國媒體,公開質疑「開羅宣言」的國際法效力,倡議「台灣地位未定論」。主張台灣應交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公開與國務院的政策唱反調。
事實上,在國務院系統內,「副領事」只是個「人微言輕」的基層外交官。但是,這位曾在台灣教過書的副領事,看在當年見識未廣的台灣人眼中,卻誤以為他有一言九鼎的份量。甚至誤以為葛超智的言行就是反映了美國的立場。
另一方面,葛超智也藉由反映這些台灣人的言論,或是間接操作集體陳情抗議的行動,來強化他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乃至於美國國務院中的發言份量。
葛超智認為台灣被美國背叛
228事件發生後,葛超智曾很焦慮的連寫了好幾篇報告,一再急切的呼籲美國應迅速介入,然後把台灣交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這三份報告,分別題為:
「台灣危機的回顧」、
「台灣起義的組織與領導」、
「中國政府在台可選擇的替代方案」
但是,美國領事館的領事布雷克 Ralph J Blake 卻在加註意見中,認為葛超智對台灣的觀察有「特定評價」,不予認同。
後來接替布雷克的第二任領事克倫茲Kenneth C.Krentz到任後,閱讀了葛超智的報告後,也認為他「思考太過情緒化,失去對當地民眾公正判斷的可能」。
而美國大使館參贊巴特沃斯W.Walten Butterworth也在葛超智的呈文中指出「他的評論措辭過於武斷與刺耳。」
葛超智雖然非常積極地想要爭取對228事件的「話語權」。但是他得到的「答案」,卻是要他立刻離開台灣,並被解職回美。葛超智從此結束了他短暫的外交官生涯;但卻空留下一群懷著「美國夢」的台灣菁英,在後來的鎮壓下,引頸就戮或陷入囹圄。直到將近二十年後,葛超智才寫了這本題為「被背叛的福爾摩沙」Formosa Betrayed 的書,總結了這段228的悲劇。
葛超智從不認為自己要負什麼「道義責任」,他舉出當時剛成立的「美國新聞處」所印發的宣傳小冊為例;指出:「華盛頓當局要求在台灣普遍宣傳美國式的生活及美國式的民主。」他們給了當時台灣菁英一個印象,似乎美國政府「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台灣實現民主制度。」葛超智還不經意的洩漏了駐台美新處主任卡竇與他的看法是一致的。
也許葛超智和卡竇的言行立場,太公開鮮明了,因此,連英國駐淡水領事館的官員都注意到了。該館的軍事參贊米勒中校K.E.F.Miller在致南京大使館的電文中就曾指出葛超智與卡竇都想辭職回美,以「發動新聞界聲援,揭發國民黨的腐敗與殘忍」。因此,當鮑威爾來台後,可想而知,卡竇非常可能會將葛超智的觀點和「備忘錄」提供給他參考。
事實上,葛超智始終認為他們所傳遞給台灣人民的訊息,並未超出美國政府這些宣傳小冊的內容。但是,當台灣人民「效法」美國革命,「揭竿而起」時,卻發現:美國政府「言行不一」,「福爾摩沙被背叛了」。這就是葛超智以《Formosa Betrayed 》為其書名的意旨所在。
「密勒氏評論報」的特殊背景
《密勒氏評論報》是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 駐遠東記者托馬斯•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1917年在上海創刊。1919年起由約翰•班傑明•鮑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 接任發行人,並自兼主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密勒氏評論報》一度遭日軍查封,直到二戰結束後,才在1945年10月,復刊。並由老鮑威爾的兒子約翰•威廉•鮑威爾夫婦接手。
老鮑威爾本來是很支持國民政府的,但自1935年,他到當時的蘇聯遠東地區和莫斯科作了一趟旅行訪問後,老鮑威爾的政治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 根據美國學者 Neil L. O'Brien.在他所著:《 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 》指出: 1936年6月,老鮑威爾指派《密勒氏評論報》的記者 愛德加•史諾 Edgar Snow ,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帶著用隱形墨水寫的介紹信函、兩架相機、24個膠卷和足夠的筆記本,進入陝北保安(今志丹縣)成為第一位訪問中共陝北根據的西方記者。 斯諾從7月初到10月中旬,對陝北作了廣泛而深入的採訪。並與毛澤東進行了多次的徹夜長談。這也是美國記者對中共領導人第一次的貼身訪問。 隨後《密勒氏評論報》將斯諾與毛澤東談話全文,和對陝北的訪問見聞,以《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為題,在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分兩期登出。並刊登了斯諾所攝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的照片。這也是毛澤東在西方世界第一次「亮相」。
斯諾在文章中把中共形容成中國的「土地改革者」,並向西方世界生動的講述了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以及中共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從而把中共形塑成「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這就是後來老鮑威爾及其《密勒氏評論報》所支持的對象。
「紅星照耀中國」重塑中共形象
作為一個「電腦科學」教授,翻譯「台灣的血浴」的李中志教授,顯然沒讀過研究中共黨史者必讀的名著《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本原翻譯為「紅星照耀中國」,後改名為「西行漫記」。這本影響深遠的書,就是《密勒氏評論報》的記者 愛德加•史諾 ,以他訪問延安的基礎上,在1937年7月寫成出版的。
繼史諾之後,西方有一票聞名的所謂「自由派」左傾記者,包括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海倫•福斯特 HelenFoster、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等等,都與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先後有過相當的淵源。
由於《密勒氏評論報》後來幾乎成為中共面向西方世界的宣傳喉舌,因此,1949年中共奪取全大陸後,《密勒氏評論報》是唯一一個能夠繼續留在上海出刊的西方媒體。
1950年,《密勒氏評論報》改為月刊。因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共產黨,並在韓戰期間成為指控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最重要的西方傳播者。《密勒氏評論報》還被中朝軍方用來對美國戰俘的政治教育素材。因此,遭致西方多國抵制禁運,致使《密勒氏評論報》難以為繼,最終於1953年6月停刊。
鮑威爾曾以「叛國罪」遭起訴
鮑威爾夫婦回美國後,1954年初,聯邦調查局向司法部刑法司建議起訴鮑威爾。同年9月和12月,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兩次傳訊鮑威爾;指控他傳播了反對美國的虛假報導。調查延至1959年二月,鮑威爾以「叛國罪」被起訴。最後因美國司法程序,對「叛國罪」的認定,要有兩個以上的證人作證。檢察官提不出證人名單,該案終於在1961年以不起訴落幕。
雖然,美國的法院未能完成對鮑威爾的控罪。但是社會大眾卻讓他始終背負著「叛國」的罵名,使他在美國傳播界再無立足之地,僅能藉著中古屋買賣度其餘生。
客觀還原真相才能實現轉型正義
綜上所述,鮑威爾及其《密勒氏評論報》是否是客觀超然的媒體或媒體人?應該是值得我們在追求「轉型正義」時,要特別謹慎判斷之處。因為,在英美法學上,對於「衍生性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有所謂「毒樹果實理論」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理論的邏輯是:如果證據的來源(樹)受到汙染,那麼任何從它衍生獲得的證據(果實)也會受到汙染。因此,這樣衍生出來的證據,在訴訟中不具備證據能力。
換言之,如果鮑威爾及其《密勒氏評論報》有他特定的政治立場,特別是,他們的立場是和國府站在對立面時,我們在引用他們的報導時,就要特別謹慎,以免誤採「毒樹果實」,而影響到「轉型正義」的客觀性。
其次,就算我們「不以人廢言」的角度,來審視鮑威爾「台灣血浴」的228報導內容後,我們也可以從鮑威爾自陳他的消息來源,是從所謂的「外籍目擊者」那裡取得的,可以確認這是一篇完全根據「傳聞」所加工作成的「新聞報導」。
在英美法中,「傳聞」原則上並無證據能力,因爲傳聞之結果,容易將陳述之內容予以簡化或趣事化,加上人的記憶因時日之經過而逐漸模糊,所謂之傳聞恐與事實大有出入,甚至產生以訛傳訛的結果。
更何況,他的「消息來源」不論是葛超智或卡竇都有他們企圖要讓台灣歸於美國或聯合國託管的政治立場。而且還經過他們自己的上級「認證」,認為他們太過主觀偏頗,報告內容對台灣的觀察有「特定評價」。鮑威爾據以報導,自然也會產生「毒樹果實」的結果。
*作者為前國大代表,「印度風」企業集團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