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人生》,拉許是身手不凡的建造師,能為任何工程畫龍點睛,同時也和藹可親。這意味透過拉許,喬伊擁有豐富的虛擬社交生活。
這讓他得以和各式各樣平常碰不到的人接觸—藝術家、知識分子、作家、生意人。拉許常獲邀參加分身們的吃喝玩樂、跳舞聊天。每當參加正式集會,拉許都會為盛會製作精美的(線上)剪貼簿,送給分身主辦人當禮物。
在我和喬伊碰面的前一週,拉許參加了一場《第二人生》的婚禮。
兩個分身結為連理,請拉許替他們戴戒指。喬伊很高興地接受邀請,並為婚禮設計了一套別致的大象晚禮服。既然列在婚禮邀請卡上的服裝標準是「有創意的正式」,喬伊便用五彩繽紛的布料來製作西裝。喬伊給我看了他在會後製作的螢幕截圖相簿—拉許也把它送給新郎新娘當禮物。拉許的慷慨吸引人們接近,還有他冷靜的情緒。在現實生活中,喬伊是個知足的男人,而這種心理狀態也投射到遊戲裡。或許正是這種平靜吸引了諾麗—扮成憂鬱法國女人的《第二人生》分身。諾麗最近都在跟拉許聊自殺的事:現實生活的自殺。喬伊和我坐在他的電腦前的那一天,他才剛以拉許的身分花了好幾個小時「駁倒她」。
諾麗告訴拉許他們的談話對她有幫助,這讓喬伊非常高興。他也很擔心她。有時他會想像自己是她的父親,有時是哥哥。但自從兩人在《第二人生》建立完整的關係,諾麗真實性的問題始終不清不楚。但最近喬伊對此憂心忡忡。她到底是誰?這個跟他說話的憂鬱分身諾麗,本人也是個憂鬱的女子嗎?或者諾麗背後的玩家跟她判若兩人,只是在線上「扮演」憂鬱的人呢?喬伊說如果諾麗的本尊不是法國人,他覺得「無所謂」,那似乎不算背叛;但如果花了好幾個小時為一個自稱想自殺的女子提供諮詢,結果「只是一場遊戲」—感覺就不對勁了。雖然他的忠告是透過拉許給諾麗的,但喬伊認為,那也是從身為人類的他,傳遞給一個自稱憂鬱、在背後操縱諾麗的女子。
在遊戲裡,喬伊習慣依照「介面價值」來看待人。照他的說法,那就是分身在線上世界表演的內容。他也希望別人這樣看待他,他想要被當成一頭異想天開、既是好友又是程式設計高手的大象來對待。但喬伊也一直跟諾麗討論那個分身背後的真實人物可能會死的事,而就算他不認為諾麗百分之百是她表現出來的樣子—至少她的真名一定不是諾麗,一如他不叫拉許—他仍希望她的本尊跟分身不要差太多,這樣他才值得投入那麼多時間經營這段關係。在勸她的時候,他當然是「真正的他」,他相信他們的關係具有某種意義,值得他這般付出;但如果她是在「表演」憂鬱,就以上皆非了。或者,就此事而論,如果她是個他的話。
喬伊意識到他這樣跟諾麗發展虛擬關係猶如走鋼索。不過他也承認,遊戲基本規則並不明確,沒有任何契約規定分身必須「忠於」玩家本身的事實。有些人創造了三、四個分身來演出自我的不同面向、與本身不同的性別或年齡等等。這喬伊都知道,但他背道而馳。最近,喬伊現實世界的名片也印上他《第二人生》的分身名。
我們可以猜到喬伊為什麼不喜歡電話。他打或接電話時,感覺都既不耐又煩躁。他說電話「干擾太大」,他比較喜歡傳簡訊或即時通。《第二人生》的分身彼此間可用文字訊息和話語即時通訊,但因為玩家常進進出出,這是個訊息不同步的地方。當我看著喬伊玩「第二生命」時,他迅速瀏覽數百則訊息,彷彿在有層次的太空中滑翔。對他來說,這些訊息,甚至包括數小時或數天前傳送的訊息,似乎都屬於「當下」。他把不同步當同步看待。他深諳某種資訊編排,飛快地在彈出的訊息和複雜的對話中穿梭,翻越一波波資訊的浪,優雅、從容。他一則訊息只讀一、兩句就開始回覆。在沒有干擾下,他覺得既與他人連結,又愉快地孤立。

當喬伊讓它的分身「靈魂出竅」,不帶軀體飛越《第二人生》時,他身在同樣位於連結與斷線之間的區域。而做這件事的時候,喬伊在遊戲裡的「自我」就不再是拉許了。喬依解釋,當他這樣飛越時,他成了一部攝影機;他的「我」成了無實質的「眼睛」,喬伊打趣說他「無軀體」飛越《第二人生》是種「超越分身的經驗」。他提出一個倫理問題:只有一些「專家」可以像他這樣飛,而當他這樣飛時,其他人看不見他,也不知道他正在注視他們。喬伊承認這是個問題,但並不在意。他對他的特權感到自在,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會濫用。他自認是親切的照顧者,他的「眼睛」屬於一個在山頂俯瞰城市的超級英雄。另外,喬伊說這不是人生,這是一場需要一套技能的遊戲,而人人都可不受約束地學習那些技能。像一隻隱形的眼睛飛行就是這樣的技能。他付了該付的費用,而這賦予他從事一項活動的權利—換個背景即可能被視為間諜活動的權利。
三十三歲的財務分析師瑪麗亞也可以化為「眼睛」飛越《第二人生》,但她在虛擬世界最享受的是,那裡的人生被放大了(writ large)。
「《第二人生》的樂趣是強化的經驗,」她說。時間加快,關係發展也加快。情緒暴衝:「從邂逅到墜入愛河到結婚到激情分手的時間,全都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發生……在《第二人生》很容易找到人聊日常生活的無聊。不過在《第二人生》,凡事都過度刺激了。」瑪麗亞解釋道:「那個世界促使人們著重大型情緒指標,那兒有戀愛、婚姻、離婚—許許多多情緒頂點被壓縮在那個世界的一個小時裡……你會一直關注重大的事情。」你聽到的話盡是「我想(虛擬地)自殺、我想結婚、我戀愛了、我想群交。」喬伊和瑪麗亞都說他們在離開遊戲後,需要時間來「減壓」。依瑪麗亞看來,《第二人生》不像人生,或許是快轉的人生。不過,瑪麗亞形容最累人的一件事是「循環利用人們」,卻被其
他《第二人生》的玩家形容為最能長久維繫的。對他們來說,線上世界的樂趣在於那是「認識新朋友」的地方。
《第二人生》給三十七歲的諾拉一種不斷嘗新的愉悅感:「我永遠不知道我會在『世界』遇到什麼。」她拿這和她在家有兩個學步兒的日常生活作對照。「在家裡我永遠知道會碰到誰。如果跟孩子待在家,誰也碰不到。或者如果我帶孩子去公園,會碰到一票保母;如果我帶他們去Formaggio(知名的美食供應商)買東西或去Hi-Rise(知名的咖啡館/烘焙坊)吃點心,會遇到一票無聊的貴婦媽媽—我猜她們都跟我一樣。」諾拉對她的生活感到乏味,但對《第二人生》不會。她這麼描述她的線上連結:「一定言之有物,總會有我真正感興趣的事。」但既然是因共同「興趣」而連結,就代表當諾拉的「興趣」改變,她就會棄人們而去。她承認她《第二人生》的友誼來得快去得也急:「我會甩人……我交朋友,然後頭也不回地走……我知道這對我的名聲不大好,但我就是喜歡永遠有新朋友。」三十一歲的建築系學生愛麗莎也有類似的經驗。她這麼說《第二人生》:「總是有其他人可以聊,有其他人可以認識。我不覺得需要什麼承諾。」
《第二人生》的分身提供虛擬青春和美貌的可能性,以及青春美貌所賦予、在現實生活非唾手可得的性接觸和浪漫交往。這些或許可用來為真實世界的邂逅增添自信,但有時似乎熟能生巧。有些《第二人生》的公民自稱已找到性、藝術、教育、接納和其他事物。我們再次聽到熟悉的故事:螢幕上的生活從聊勝於無,進化成無與倫比。在這裡,自我可以千變萬化、令人放心地分飾多角。你可以試驗各式各樣的人,卻不必承擔真實關係的風險;如果你覺得無聊或惹上麻煩,你大可如同諾拉所說:「頭也不回地走。」或者你可以讓你的分身「退休」,另起爐灶。
愛你的《第二人生》會讓你放棄抵抗現實生活的失望嗎?現在,如果你找不到好的工作,你可以想像自己在虛擬世界裡功成名就。你可以逃離令人憂鬱的公寓,在模擬的別墅裡款待賓客。但是,儘管對某些人來說,虛擬或可減輕不滿,但對其他人而言,那似乎只是一種排憂解悶的方式。「研究所時我玩《魔獸世界》玩了四年,」三十二歲的經濟學者雷尼說。「我喜歡當中的冒險、謎題和推理,我喜歡和各種不同的人合作。我曾和一個來自紐約的舞者、一個來自亞利桑那十六歲的數學天才和一個倫敦銀行家一起尋寶。他們的觀點都好有趣,我們的合作美妙極了,那是我有生以來最棒的經歷。」現在,結婚生子的他,一有時間就會溜回《魔獸世界》。「那比度假更棒,」他說。他在研究所時期覺得遊戲超棒的特性依然沒變:那是他最快、最穩當認識新朋友和找到刺激、挑戰的方式。「度假嘛,可能有幫助,也可能沒有,《魔獸世界》保證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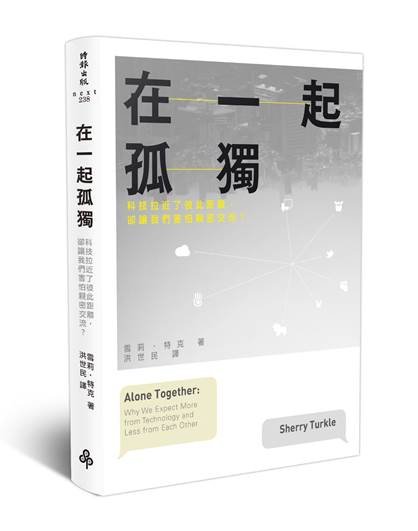
*本文取自時報出版《在一起孤獨》一書,作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現居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MIT)科技社會研究教授,MIT科技和自我創新計畫(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創辦人兼主任,也是有執照的臨床心理學家。投身科技心理研究超過三十年,被凱文.凱利譽為科技界的佛洛伊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