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有外省籍的老爺子要單獨坐計程車,家人會再三的叮嚀他:「不要在車上胡亂批評政治,說什麼台獨的壞話。如果你被嗆在台灣住了幾十年,台灣話都不會講,被趕下車,叫你乾脆回大陸去住。我可救不了你。」這種對老爺子的「保護措施」可能已經說超過20年了,老爺子雖然被唬得一愣一愣的,不過他心裡有數,早已經承認這是「善意的叮嚀」。雖然現在計程車司機的政治傾向也已經多元化了,在言談中經過主客彼此的試探,發現彼此是「同溫層」時,老爺子和司機相談甚歡,有了快樂的旅程也並不少見。但如果你問朋友談起另外一個話題:「你跟你的孩子談政治嗎?他跟你的看法一樣嗎?」得到的答案十之八九好像都是頗為無奈的。比如「說沒兩句就吵起來,徒傷感情,這何必呢?」就差個沒有像老舍《茶館》裡一樣,在家裡掛起「不談國事」的小牌子。這不是票投給誰的問題,而是大家有意無意都在尋求同溫層,包括親子之間,不在同溫層上好像就有了一層隔膜。
居然有一種東西叫做「政治正確」
同溫層與同溫層擴大結合之後,就形成了一股「氣流」,這種氣流迴盪久了就變成「氣候」,政治氣候會變來變去的,我們說的「政治正確」也是變來變去的。台灣的政治氣候從兩蔣威權時期的「反共」,一直到兩岸開放交流之後的「親共」或不再那麼「仇共」,到現在的全民「恐共」都各有其政治背景,也都形成不同時代的「政治正確」。各種主張也在言之成理的背後,每個人的故事各有恩怨情仇,不容易化解。
一個在中國的戰亂中一路被軍隊拉伕,衣衫襤褸地來到台灣,發生像電影《香蕉天堂》情節的老芋仔;一個在日據時代讀書永遠不能考第一名,經常被日本同學霸淩的台灣「公學校」的小學生;一個在台灣光復,跑到火車站敲鑼打鼓迎接祖國軍隊的台灣大學生;一個在228事件發現白色祖國靠不住,為了救國而投向紅色祖國加入共產黨的熱血青年;一個在白色恐怖時期因為看了賽珍珠的《大地》、魯迅巴金茅盾的小說,莫名其妙地被吉普車帶走,關進大牢的知識青年;一個在美麗島事件大審高舉六法全書在法庭上為台灣的言論自由辯論的年輕律師;一個獻身台灣黨外運動,現在看到「鐮刀派」的民進黨小輩違背他們當年革命理想的老革命者等。這些在台灣這一塊相同的土地,在不同時代所孕育出來,數不盡的政治難民、流亡學生、被殖民者、政治理想主義者等,各有各的人生故事,各自經歷了不同的苦難。現在他們都老了,卻發現這個社會居然有一種東西叫做「政治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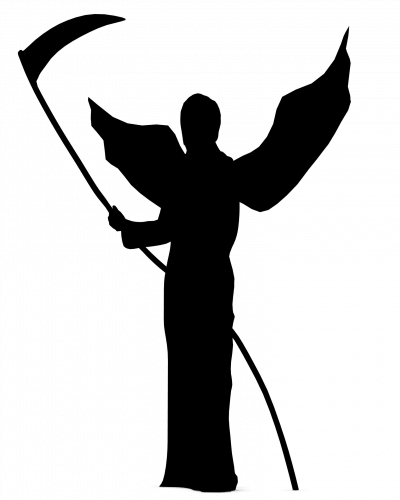
一把割傷歷史的鐮刀,朝向苦難台灣的身上揮去
他或許只能茫然地對你說 :「什麼是政治正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老老實實地走過我的一生。你吃的苦我不知道;我受的罪你也不清楚.。我們都『不正確』了嗎?」當他們害怕在大庭廣眾之下真實地說出自己的故事而被人白眼;當他們發現自己的故事,孫子們不屑一聽時,你說他們心裡有多大的悲傷呢? 「政治正確」, 就像一把割傷歷史的鐮刀,朝向苦難台灣的身上揮去。
現在,這些台灣歷史苦難的先行者,他們可能與當年漫長等待他從綠島歸來的老妻隱身在陋巷;可能每天守著眼前發亮的小盒子,看電視播出各類名嘴口角白沫指天畫地;可能靜靜地坐在某個候選人造勢場下面一張紅色的塑膠椅上。相同的是,他們都錯愕地發現自己的故事被化約成一種自己感到既熟悉卻陌生、似陌生卻熟悉的「政治正確」。不同的幾群人,把他們的「政治正確」強加在別人的身上。
「政治正確」被當成一種政見「廣告」
台灣每年都有選舉,當選舉成為年度最大的買賣的時候,「政治正確」被當成一種政見廣告。政客為了收買人心所說的話,說開的支票都與廣告無異。 儘管這些政客所推出的「政見廣告」一看就知道非常愚蠢,但是因為政客看準了選民都是愚蠢,他只要確定推出的「政見廣告」是符合消費者的口味就可以了。
拿破崙曾說:「政治上,愚蠢不是一種劣勢。」原因一方面在於政客必須取得大部分是蠢人的民眾的歡迎。所以,一個不愚蠢的政客也必須裝得很蠢;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的演技並不出神入化,那麼他的表演一定沒有自然行為更具說服力,也就是說,在政治中不愚蠢就是一種妨礙。當歷史成為政客攖取政治利益的工具的時候,歷史就成為政客做廣告非常有效的內容。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在《理解媒介》中寫道:「廣告已經成了真正的商品,商業的目的不再是生產商品,卻變成了推銷商品。」當作家只寫作品評論卻不寫書,就像政客只唬爛政見卻不談政見一樣。我們看到的選舉,政治人物候選人比賽的不是誰的政見比較好,而是誰推銷這些「政見謊言」的技術比較高明,也就是看誰做的「政見廣告」比較受人歡迎。
作為「實際商品」貌似真實、實則虛假的圖像,廣告就是一種形而上的愚蠢;作為「政策買票」貌似真實、實則虛假的圖像,政見也是一種形而上的愚蠢。但當它塞滿每一個談話性節目名嘴的嘴巴;潛入我們的電子郵箱;湧入網路新聞的角角落落,全面入侵我們的生活時,就成為了一種「形而下(看得見)的愚蠢」。與其相比,獨裁政治的宣傳就更是個笑話了,而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則厭惡地說:「廣告就是攪屎棍攪動時的噪聲。」顯然地,華而不實的政見亦復如是。

忍受從天傾倒下來的垃圾
「政治正確」瘋狂的流行,並沒有像流行性感冒一樣那麼張狂;相反地,它是透過慢慢地制約,利用人們渴望在和諧的生活當中不被認為太過突兀的從眾心理,而慢慢地使人不知反抗地自我約束所形成的。比如在台灣,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統治的時代,學生演講比賽題目不是講「如何粉碎共產黨統戰的陰謀」,就是講「復興中華文化之我見」,學生的思想被塑造成任何時刻即席演講,對這樣的刻板題目都可以琅琅上口講個十分鐘,下了台連自己講些什麼都搞不清楚。「政治正確」的可怕之處,不在於那些少數幾個人出這種愚蠢題目給學生來演講的老師;也不在於像開水龍頭一樣說出一些莫名其妙蠢話,那些被洗腦的學生;而在於那些台下眾多的觀眾像吃了麻藥一樣,可以乖乖地忍受從天傾倒下來的垃圾而無動於衷,甚至逐漸信以為真。政治的愚蠢只需通過平常的言行來表現。而所謂的「政治語言」即言之無物的藝術,又使這種愚蠢得以昇華。
利用別人的傷痛來製造仇恨,令人不恥
「政治正確」的旗幟,你愛怎麼霍霍招展沒人管你。不過,如果拿它來硬套在別人頭上,或是利用別人歷史的傷痛來製造仇恨,那就令人不恥了。比如說,有一些人愛叫人饒恕過去,那是很無情幼稚的。這些人應該去看一看「國家人權博物館」訪問當年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系列影片,聽一聽這些被國民黨特務無端地羅織罪狀,在牢裡度過五年七年十幾年歲月,甚至被槍斃,搞得家破人亡,親友長年不敢跟他們往來的故事。然後,自問如果你是當事人或是他的後代家屬,你可以輕易忘記那段悲慘的故事,輕易地去饒恕那些加害者嗎?當我們和偶爾並肩坐在一起的某人談起眼前的台灣選舉時,倘若我們毫不在乎此人的過往人生,而喋喋不休地陳述以為「人人皆知」的政治觀,自以為的「政治正確」,這是多麼無禮而冒犯啊!
歷史不是「人人皆知」的故事。
寫過《再見,哥倫布》(Goodbye, Columbus)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菲力浦羅斯(Philip Roth,1933-2018)在他的另一本書《人性汙點》(The Human Stain)中描述了一場「迷信的盛大狂歡」,在那裡,「無論是言行浮誇的還是品行端正的無賴,都急不可耐地想批評、譴責和懲處,佔領道德的制高點。」本書一開場就有一個「人人皆知」的諷喻,作者透過故事告訴我大家,人們自以為知道所有在眼前發生的事,卻一無所知背後屹立不動的祕密。他說: 「人人皆知是陳詞濫調的援引……人人都一無所知。你什麼都不可能知道。……我們所不知的一切令人驚訝;而更令人驚訝的是自以為知的一切。」
是的!歷史不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你的歷史,不同於我的歷史。我們要對被無端傾倒在身上的「政治垃圾」表示抗議。或許有些事、有些人,我們如何都無法饒恕;但是,我願意學習尊重,也期待你學習尊重。尊重也是一種饒恕,至少是饒恕的起點。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