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來,建築物越來越高聳,有限的土地在容納更多人的同時,卻不用逼迫這些人擠在如棺材般大小的房間裡,就像東京遠近馳名的膠囊旅館一樣。不過,直到十九世紀為止,往上發展的速度相當溫和,頂多是用四層到六層樓的建築取代兩層的矮房子。這段時期,高度主要受限於建築成本,以及人類對攀爬樓梯的忍受度。教堂的尖塔與鐘樓可以蓋得高聳入雲,因為它們的內部空間非常狹小,而且只有極少數人才需要攀爬上去,例如敲鐘人。高層建築在十九世紀之所以能夠出現,主要是因為美國發明家解決了這兩項難題,可以不需要加厚底層的支撐牆,又可以讓人員安全往返各個樓層。
艾利沙.歐提斯(Elisha Otis)並未發明電梯;據說是兩千兩百年前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西西里島建造了第一座電梯。路易十五在凡爾賽擁有一座個人電梯,用來與情婦私會。不過,電梯要成為大眾運輸工具,除了需要動力來源,也需要安全。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與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提供早期蒸汽引擎做為工業電梯的動力,在此之前要不是以繩索拉動,就是以水力推動。隨著引擎的改良,電梯的速度與動力也跟著改善,可以從礦坑裡運出大量的煤,或從船艙裡運出大量的穀物。
但是人類還是很害怕搭乘電梯前往比較高的樓層,因為電梯很容易損壞,也許會讓他們從高處摔落到地面。而這項問題在歐提斯手中獲得解決,他是紐約州雍克斯(Yonkers)鋸木廠的銲接工人。歐提斯製造的安全煞車不僅可以裝設在電梯設備裡,也可以安裝於火車上。一八五三年,他帶著這項發明參加在紐約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他讓自己站在平臺上,平臺由繩索拉著,接著有人戲劇性地拿斧頭砍斷繩索。平臺略為往下掉,但由於裝設了安全煞車的關係,平臺很快就停了下來。歐提斯的電梯馬上引起轟動,而他的公司也成為電梯的世界領導品牌。

一八八五年,威廉·勒·巴隆·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於芝加哥建造了高一百三十八英尺的家庭保險大樓(Home Insurance Building),這棟大樓通常被認為是第一座真正的摩天大樓,但詹尼是否真是摩天大樓的首創者,建築界對此仍存在激辯。這場辯論反映出摩天大樓的發展就像城市絕大多數的特質一樣,並不是在社會真空中發生,亦非一蹴可幾。詹尼的「第一座摩天大樓」不完全是鋼骨建築。它只有兩面鋼筋防火牆。兩年之前,丹尼爾.伯爾南姆(Daniel Burnham)與約翰.魯特(John Root)也在芝加哥完成了蒙托克大樓(Montauk Building),這棟大樓也使用了鋼筋。工業建築,如紐約的麥克庫洛彈丸製造塔(McCullough Shot Tower)與巴黎附近的聖圖安碼頭倉庫(St. Ouen Docks Warehouse),在數十年前就已使用了鋼骨構架。
詹尼建造的原始摩天大樓是一項拼湊品,他把芝加哥許多建築師的觀念,連同自己的發明一起結合起來。其他的建築師如伯爾南姆與魯特、他們的工程師喬治.富勒(George Fuller),與詹尼之前的學徒路易斯.蘇利文(Louis Sullivan),進一步發展這種觀念。一八九○年,蘇利文做出重大突破,他在聖路易斯設計了溫萊特大樓(Wainwright Building),省略了大量裝飾用的石造建築。詹尼的建築物是維多利亞式的,但溫萊特大樓卻清楚朝現代主義高樓發展,而且成為現在許多城市天際線的特徵。
他們的集體創造──摩天大樓使城市能在相同的土地區域上增添樓地板面積。在市中心房地產需求增加的情況下,摩天大樓就像個天賜之物。問題是這些市中心上面已經蓋了大樓。除了芝加哥這種因為大火而創造出一大片空地的城市,其他城市都必須拆掉舊建物才能進行建設。
紐約對空間的需求更甚於芝加哥,於是摩天大樓很快就出現在曼哈頓。一八九○年,普立茲的世界大樓運用了鋼柱,但它的重量主要還是仰賴七英尺厚的石牆支撐。一八九九年,以鋼骨支撐高度達三百九十一英尺的公園街大樓(Park Row Building)超越了世界大樓。一九○七年,伯爾南姆在美東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熨斗大樓(Flatiron Building);一九○九年,威特的國家設計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被拆除,原地改建為七百英尺高的大都會人壽大樓(Metropolitan Life Tower),這是當時世界最高的建築物。一九一三年,伍爾沃斯大樓(Woolworth Building)達到七百九十二英尺,直到一九二○年代末,它一直是世界最高的建築物。

對高度的恐懼
二次大戰後,紐約加強管制建案與租金,因而使民間開發更加困難。紐約另行提供大量的公共補助建案,例如史岱文森鎮(Stuyvesant Town)與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但到了一九五○與六○年代,無論是公共還是民間計畫都逐漸受到草根組織者(例如珍.雅各)的反對,他們越來越善於發起運動反對大規模開發案。
珍·雅各與大城市的榮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一九三四年,她畢業於斯克蘭頓(Scranton)的中央高中,隔年她前往紐約,因為她認為紐約會比東北部的賓州來得有趣。珍.雅各到哥倫比亞大學上推廣課程,但並未取得大學學歷。日後她還婉拒許多大學頒給她榮譽學位。我跟珍.雅各首次見面是在一九九三年,我對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對於自己自學成功感到自豪。珍·雅各最早是以自由作家的身分在《先鋒論壇報》(Herald Tribune)上針對紐約市發表文章。她的地位逐漸提升,最後成為一本專門討論建築的月刊《建築論壇》(Architectural Forum)的副總編輯。她嫁給建築師羅伯特·雅各(Robert Jacobs),然後決定在西村(West Village)的哈德遜街(Hudson Street)生兒育女。
珍·雅各直到八十幾歲依然思緒清楚,她過人的才智與她在紐約市的經驗,產生許多深刻的先見之明。一九五○年代,她清楚看出城市更新的愚蠢,這些更新計畫打算以巨大而孤立於市街之外的高樓來取代功能良好的社區。珍·雅各反對既有的城市計畫思維,這些計畫想創造單一功能的鄰里,而珍·雅各支持多元發展。一九六○年代,她領悟到城市在傳播知識與觀念,以及創造經濟成長上扮演的角色。一九七○年代,她了解城市其實比充滿綠意的郊區對環境更有利。她的洞察力來自於她是一名極具天賦的觀察者,而她生活與工作的地方又在紐約。她的知識來自於她以步行的方式巡迴街頭,而且張大了眼睛仔細觀察,這種方式至今仍是了解城市運作的最佳途徑。
珍·雅各反對城市更新,這種立場使她極為厭惡高層建築。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中,她認為城市社區要繁榮,每英畝必須居住一百到兩百個家戶。城市裡每英畝至少要住有一百個家戶才能產生足夠的交通流量來維持餐廳與商店的活力。她也認為每英畝兩百個家戶是個「危險信號」;一旦社區密度超過這個臨界數字,就可能喪失活力死氣沉沉。曼哈頓典型的公寓,例如我成長時期居住的地方,樓地板面積大約一千三百平方英尺。如果每英畝要容納兩百個家戶,則建築物必須要有六層樓高,這約略等同於電梯時代來臨前公寓的標準高度。

珍·雅各也許很了解自己生活的低矮社區的好處,但我們不確定她是否了解高層建築的活力所在。曼哈頓高聳社區的一樓店面如果能有充足的活動,則這個地區並不會像珍·雅各所說的那樣死氣沉沉。高層社區也可以有許多有趣的商店與餐廳。每英畝三百或三百以上的家戶,這樣的密度或許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但人口的多樣性會產生各種生活需求,而有些人的確想住在高層建築裡。珍·雅各個人偏好格林威治村風格的社區,這一點不難理解,我也喜歡格林威治村,但個人的喜好並不能做為公共政策的基礎。由政府發號施令推動單一風格的城市主義,就跟政府強制推行單一風格的文學一樣不合理。
珍·雅各想保護老建築物,但她的經濟推論似乎出現了混淆。她認為保留老舊低矮的建築物,可以壓低房價,使剛開始創業的企業家可以負擔。然而這種說法顯然違背了供需法則。保留老舊的單層房屋而不讓它改建為四十層高的大樓並不能壓抑房價。事實上,反對興建新大樓必定會造成人口稠密地區房價居高不下。房屋供給量增加,幾乎總能讓房價下跌,相反地,限制房地產供給只會讓房價攀高。
房屋供給與房價的關係不僅僅是經濟理論的問題。空間供給與房地產成本之間的關係其實相當複雜多樣。但簡單地說,房價高的地方建物稀少,而大興土木的地方房價不會太貴。有幾篇報告顯示,新建物能降低房價,而限制建設的地區房價提高。其中一篇論文很聰明地以建築的自然障礙,如丘陵地來說明,地形崎嶇的地方比較少有新的建物,因此房價偏高。
或許新蓋的四十層建築物不一定願意容納經營不善獲利微薄的公司,但藉由新空間的提供,可以緩和城市其他地區房地產的壓力。城市更新造成的房價上漲現象,可以透過新建物的提供來加以緩和。新建物的成長使空間的價格變得可負擔,並且確保窮人與獲利較少的企業能夠留下,這有助於讓正在發展的城市更加成功與多元,而非限制建築高度與固定住房數量。高度限制確實能增加日照量,而保存舊建物也的確保護了歷史,但我們不應該佯裝這些好處毫無代價。
三項簡單的原則
我們的城市做為世界經濟的引擎,它們的成功逐漸取決於土地使用分區委員會與保存委員會做出的艱深難懂的決定。在稠密的城市空間管控建設當然是合理的,但我會以三項簡單的原則來取代現在用來限制建築的各種雜亂無章的法規。
首先,城市應該以簡單的收費制度來取代現今冗長而不確定的批准過程。如果高樓因為遮住日光或阻擋視線而導致了成本增加,那麼對這些成本進行合理估算之後,再向建商收取適當費用。如果某些活動對鄰居有害,那麼我們應該估計社會成本而向建商收取費用,正如我們應該向駕駛人收取交通堵塞的費用一樣。這些稅捐應該轉交給那些受害者,例如因為新建案而失去陽光的鄰近住戶。
我不認為這些制度可以輕易地設計出來。各種高度的建築物造成的成本多少,這當中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人們一定會對可以獲得補償的鄰近地區大小發生爭執,因此我們應該發展一套放之四海皆準的合理原則。舉例來說,紐約每一棟新建築的建商每平方英尺要支付一定金額做為補償成本,以儘速獲得主管機關批准。這筆錢有部分流入市庫,其餘部分則給予新建築所在街廓的居民。
單一的稅捐系統要比現有的複雜管制更為透明且更能對症下藥。今日,許多建商雇用昂貴的律師與遊說團體,並且收買某些政治有力人士,以此來與現今的制度進行協商。對他們來說,如果只需要簽張支票給政府與其他住戶就能解決事情,那是再好也不過的。允許更多建案不表示圖利建商;合理而直接的管制可以讓新建案有利於鄰里社區乃至於整座城市。
其次,歷史地標的保存應該有所限制與明確界定。將熨斗大樓或舊賓州車站這類建築傑作列為地標相當合適的,但保留數量龐大的戰後玻璃磚建築則很愚蠢。然而,你要如何在這兩種極端之間畫下界線呢?

我個人的立場是,在紐約這樣的城市裡,地標委員會應該先列出固定數量的應保護建築,比如說有五千棟。委員會可以更動這些已選定的建築珍寶名單,但過程必須審慎緩慢。委員會不能在一夕之間就推翻原則,要求在未受保護地區動工的建案停工。如果委員會想保存一整個區,那麼就要讓這一整個區把五千棟的保護額度一口氣用光。或許五千棟這個數量太少,但若不在數量上設限,管制機構的規模將會持續擴大,無論是因為官僚本身就有自我增生的傾向,還是為了回應社區的壓力。
像巴黎這種廣受世人喜愛的城市,問題處理起來會更棘手。在這類城市裡,關鍵是在鄰近市中心的地方找到大片土地,然後在這片土地進行高密度開發。理想的狀態下,這個空間應該近到足以讓居民以步行的方式走進舊市區的美麗街道中。
最後,個別的鄰里社區應該要有清楚的權力來維護自身的特殊性。某些街廓的居民也許不希望有酒吧;其他街廓的居民也許求之不得。避免由上而下地對社區進行管制,比較合理的做法或許是允許個別社區在經由大多數民眾的同意下,自行訂定一套有關建築風格與用途的規則。但社區不應該擁有完全阻礙建設的權力,例如限制高度或加諸過度的管制,以免地方社區成為鄰避主義者(NIMBYist)的根據地。一般民眾應該要比市府的計畫者對於自己鄰近地區發生的事有更多的發言權,但社區的控制遺憾地必須受到限制,因為地方社區通常考慮不到禁止建設對整個城市帶來的負面效果。
偉大的城市不是靜態的──它們會持續演變並且帶領世界前進。當紐約、芝加哥與巴黎經歷大量創意與成長的噴發之後,這些城市便開始改頭換面地提供新建築物來容納新的才能與觀念。城市無法光憑新建築來造成改變,「鐵鏽地帶」的經驗已說明了這點。然而如果改變已經開始發生,那麼適當的新建築將可加速這段過程。
世界上有許多城市,無論新舊,對於高密度地區往往設下許多限制建設的規定。有時這些法規有其道理,例如保存重要的建築作品。然而,有時這些法規只是愚蠢的鄰避主義者或受到誤導想阻止城市成長的人的產物。無論如何,限制建設把城市牢牢地與過去捆在一起,限制了城市未來的發展。如果城市無法建設,那麼建設的力量就會外移。如果一座城市的建設遭到凍結,那麼成長必然將在別的城市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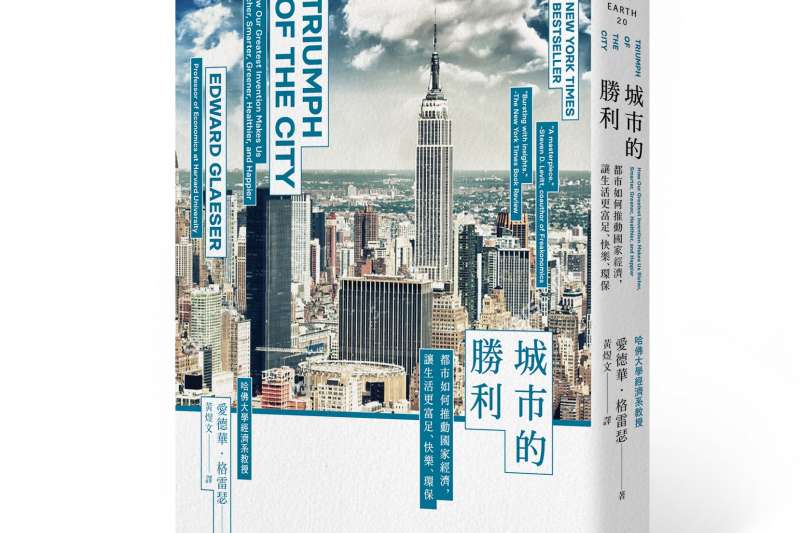
*作者愛德華.格雷瑟(Edward Glaeser)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專長為個體經濟學理論、城市和公共經濟學。研究領域包括城市、住房、種族隔離、肥胖、犯罪與創新制度等。他曾發表數十篇關於城市的經濟發展、法律和經濟學的論文。多聚焦在研究城市發展的決定因素,以及城市作為思想傳播中心的角色定位。本文選自《城市的勝利:都市如何推動國家經濟,讓生活更富足、快樂、環保?(最爭議的21世紀都市規畫經典)》(時報出版)。
































